对于基层的清洁队员而言,清运量攸关其工作绩效以及人力、预算的规模,因此宁愿高估也不可少算。反之,当以垃圾以焚烧为主要处理方式时,由于焚化厂有较精确的磅秤,而且垃圾量多寡攸关政府必须负担的费用,因此基层政府单位有动机提供相对精确的数字。这也许是我国近年垃圾减量的成效异常卓著的部分因素——从八十七年每人平均1.13公斤的垃圾量,大幅降为九十一年的0.86公斤,降幅高达27%。然而,民众环保意识抬头,各种资源回收(如保特瓶回收计划)与垃圾减量措施成效卓著,以及民间加入垃圾处理(如台塑收取厨余以生产有机肥)产业等因素也可能有重要影响,让今后的垃圾量持续下降的趋势相当明显。
垃圾焚化处理容量远大于需求量虽然是许多垃圾焚化厂营运绩效不彰的结构性因素,但地方行政疆界的藩篱,让各县市各自为政无法互通有无,才是更重要的问题。由于各县市在垃圾处理方面各自为政,同时兴建焚化厂的进度不一(有些比较顺利,有些则遭遇较大的阻挠),因此现阶段焚化厂在各个县市的供需情形也不一样:有的县市可能因面临较剧烈的抗争,无法顺利兴建焚化厂,导致目前垃圾末端处理设施的容量不足,因而对焚化厂的需求相对较高;反之,有的则因境内已有多座焚化厂,余裕处理量甚大(如高雄县有仁武、冈山两厂各1350吨的日处理量,却只有800吨的需求),却因为地方政府唯恐引起民众抗争,不愿进行跨县市的整合以改善各地「垃圾市场」供需失调情形。
此外,从财政上的角度,让垃圾在不同行政区域内自由流动也将有互蒙其利的效果。从环保署(2003)提供的资料来看,许多焚化炉委托民营事业单位代为操作。由于各类契约条件不同,代操作的费用也有相当大的差异,从最低的每吨负136元,到最高的849元,此间相差将近1000元。若能降低对高操作费焚化厂的依赖,把垃圾转到低操作费的焚化厂,则有节省公帑之效果。为了让既有焚化厂维持营运的效率,也让各县市能够透过转运降低垃圾处理成本建构垃圾管理区域合作机制乃全然合理的思考方向。但政治可行性多高?是否会激起新的邻避抗争?
肆、跨域合作管理垃圾的可能——以嘉义县市的合作机制为例
跨域合作有其困难度。赵永茂教授列举了跨区合作及管理经常面临包括政治、经济、组织等层面的限制。在政治面,可能发生中央与地方垂直政府间(或政党)的对抗(vertical confrontation)、水平政府(或政党)间对抗(horizontal confrontation)、同一政府内的行政立法冲突(internal conflict)、府际关系与府际管理法制的建立不足等问题,以及不同地区公民投票议决冲突等问题,干预跨域合作的形成。在经济方面的限制,则可能有双方合作所生之外部效益不足以提供合作之诱因、地区产业及经济衰退区的威胁、经济性机能与组织发展不足导致经济发展规划案与其它竞标外包合作案不易推动;经济发展与环境、文化、历史保护的竞争等问题。最后,行政机关本身则可能有本位主义,缺乏合伙之观念、经验、技术与组织等内在因素,都可能形成阻碍(赵永茂,2003:62)。因此,跨域合作在台湾成功的例子至今仍相当有限。
一般讨论跨域合作处理垃圾的案例,都会提及台北市与基隆市之间的合作协议——由台北市提供基隆市300吨垃圾焚化处理量,而基隆市则代台北市处理等量的灰渣,堪称为互蒙其利的双赢协议。然而,诚如环保团体所批评,此一协议背后的前提是基隆市自有之600万吨容量垃圾焚化厂仍持续建造,近期内将完工运转,届时将不再需要与台北市合作处理,颇有暂时解决基隆市垃圾处理燃眉之急的意味,并无透过跨域合作以达到最适营运规模、提升垃圾管理效率的意图,故难谓的新治理的范例。反观嘉义县市所达成的协议,虽不见媒体大肆报导,知名度远不如北基合作案例,但以其较有长治久安的企图,也有降低彼此营运成本的效果,因此十分值得深入了解,探讨这类合作案例成功所代表之多元治理上的意义。
一、鹿草垃圾焚化厂的兴建与达和公司的营运
长期以来,台湾地方政府一直十分仰赖中央政府的财政补助,地方大型公共建设更是极端仰赖补助,而争取的途径有二:一、是地方人士充分合作,以筹集资金,并借资向上级请求补助。二、是地方首长、民意代表的合作向上级争取补助(赵永茂,1978:219)。因此,派系争斗严重的地区如云林县、嘉义县等,地方首长与不同派系合作争取上级政府的建设补助,成功案例并不多见。基本上,焚化厂属于「邻避」设施,亦即不受人欢迎的设施,但这种属于区域性的公共设施,以邻避设施的特性来分析,焚化厂所生之效益为广大区域的使用者共享,但其所产生之负面外部效益则由厂址邻近区域之民众来负担,其次,设施之兴建本身属于高度专业科技知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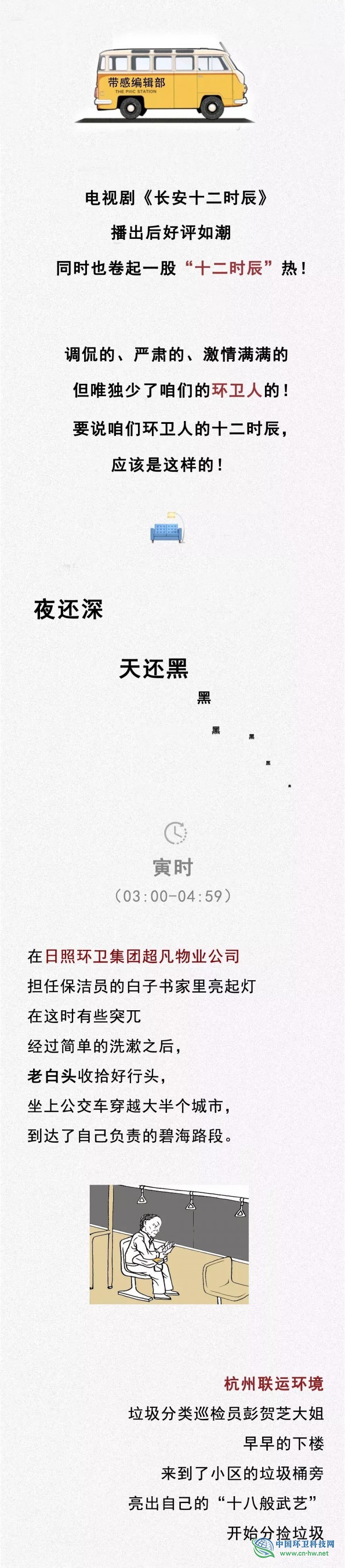

 “邻避”堡垒松动 垃圾焚烧发电进入高质量成长期
“邻避”堡垒松动 垃圾焚烧发电进入高质量成长期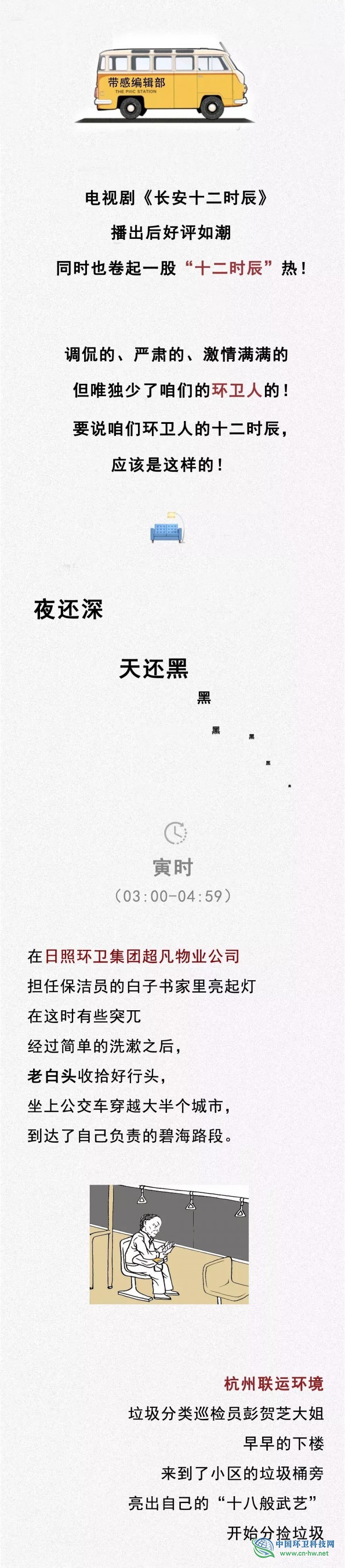 环卫人的12时辰!
环卫人的12时辰!
 环卫科技网公众号
环卫科技网公众号 乐分圈微信公众号
乐分圈微信公众号 厕重点微信公众号
厕重点微信公众号 环卫装备微信公众号
环卫装备微信公众号
 关闭
关闭 关闭
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