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废弃物处理产业在近几十年内快速蕈集成庞大集团的趋势,证明垃圾处理的规模经济显然相当可观——大公司能够整合运输、仓储、能源管理、以及资源再生使用等产业,降低营运成本,增加营运灵活度与对外谈判筹码,使得小规模经营的小公司因相对而言较缺乏效率,不是遭到淘汰、兼并,就是寻求彼此结盟以图生存。以垃圾焚化厂为例,每个垃圾焚化厂的兴建,动辄耗资数十亿元的经费;焚化厂的日常营运与维修也动辄数千万元,并涉及相当程度的专业,耗费相当可观的公务人力,除北高等财务规模较大的政府单位,实非一般地方政府有能力负担的公共设施。同时,焚化厂的运转必须燃烧相当吨数的垃圾量才能发电出售以维持损益平衡,而维持稳定的垃圾量以维持稳定的供电量之能力也让焚化厂具有较大的谈判议价空间。因此,若能整合不同焚化厂的营运以降低垃圾量供应的不确定性,将能增加营运效率。
此外,拜运输科技进步以及高速公路网发达之赐,废弃物处理的规模经济得以日益扩大,除了垃圾收集较属于劳力密集的产业,较有地缘上的考虑,其它次体系都因运输成本能够有效压低,而得以沿着特定终端处理厂址向外延伸,透过集中处理以达到更具效率的营运规模。而地方政府则透过委托外包(contracting out)等方式,让一些甚具规模的废弃物处理公司以较低廉的价格提供完整的服务,让垃圾在不同行政疆界之间自由流动,而不涉及「谁家的垃圾」与「由谁处理」的问题,似乎是较具效率的作法。
反观国内的情形,现行的垃圾处理政策正面临重大的考验。我国垃圾处理长久以来一直是最基层的乡镇市公所的职责,不但由乡镇市公所的清洁队负责收取垃圾,也由其负责找地方掩埋。此一制度设计也许因为垃圾收集、分类是劳力密集的工作,也有地域上的限制(在短时间内服务全境的需求),同时早年社会对于垃圾掩埋的卫生安全要求不高,因此允许地方政府以低成本的方式便宜行事。
在许多大型焚化厂兴建完成并顺利运转之后,垃圾处理虽有从乡镇向县市集权的趋势,同时九十三年版的「废弃物清理法」也规定,九十三年七月十四日前各县市环境保护局应完成一般废弃物工作调整,由县环境保护局统一处理,届时如能否克服乡镇市公所的抗拒,依照各乡市垃圾处理设施能力宏观地调配县市境内的垃圾,将能增加垃圾处理的效率。但纯就经营规模的角度而言,县市政府其实还不是最适(optimal)之处理层级。一方面兴建的费用本身就是几十亿元的预算,没有中央政府补助,除了北高两市财政能力稍佳之外,几乎没有地方政府能够负担这样庞大的费用。而操作经营与设备维护则涉及相当的高的专业需求以及可观的经费,往往也超过地方政府能够负担的极限。而更重要的问题是,就全国焚化厂的总处理量而言,已远远超过总需求量,但焚化厂因兴建时程的差异,在各县市之间的分布并不平均,导致有些县市有高额的余裕处理量,有些却还没有焚化炉处理自己的垃圾。由于过去十多年来垃圾焚化炉的兴建与营运都由地方政府主导,地方虽然在特定时空背景下对焚化炉有不同程度的需求,但因为早期垃圾无处可去所引发之垃圾危机是如此刻骨铭心,让各地方政府莫不希望透过拥有自己的焚化炉,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垃圾处理的问题。此外,环保署巨额补助地方兴建焚化炉的政策,也提供了重要的财务诱因,导致地方努力与地方居民达成各类补偿协议,积极弭平地方的邻避抗争,让许多地方的焚化厂都能完成兴建并顺利运转。在各焚化炉相继完工加入营运之际,环保团体开始质疑环保署核准兴建的焚化炉已超过需求量。
根据环保署的统计,台湾地区九十一年的垃圾清运总量约为675万公吨,其中56.62%(共约382万公吨)以焚化方式处理。而环保署八十年核定兴建并完工运转的18座焚化厂,若以85%的操作运转率计算,目前国内处理容量每年约已超过612万公吨。若再加上即将完工的宜兰利泽厂、基隆市厂,以及八十五年核定兴建将于近年完工的各焚化厂所拥有的196万公吨,近年内将有超过800万公吨的总处理容量,不但超过处理目前所需焚化垃圾量的两倍,即使全部清运垃圾都已焚化处理,届时处理容量也远超过所需之量。换句话说,许多焚化厂不是必须以处理事业废弃物来填补,就是将面临无垃圾可烧的窘境。而县市政府往往与焚化厂代操作厂商签订保证进厂量的契约,依目前过高保证量,对许多地方政府都产生很大的压力,可能很快就会发生政府需付费买垃圾给焚化厂,或焚化厂之间互相抢垃圾烧(以维持发电量)的现象。至于环保署当初为何核准这么多焚化厂之兴建,主要是因为受委托的学者依照当初的垃圾量以及10%的成长量推估出来的需求量过高所致,而学者则是依据环保署提供的统计资料来估算。相关的统计资料是由下级政府层层汇报至环保署。由于以往垃圾以掩埋为主时,各乡镇清洁队并没有精确估算垃圾量的能力与动机,仅能以「车」为单位概略推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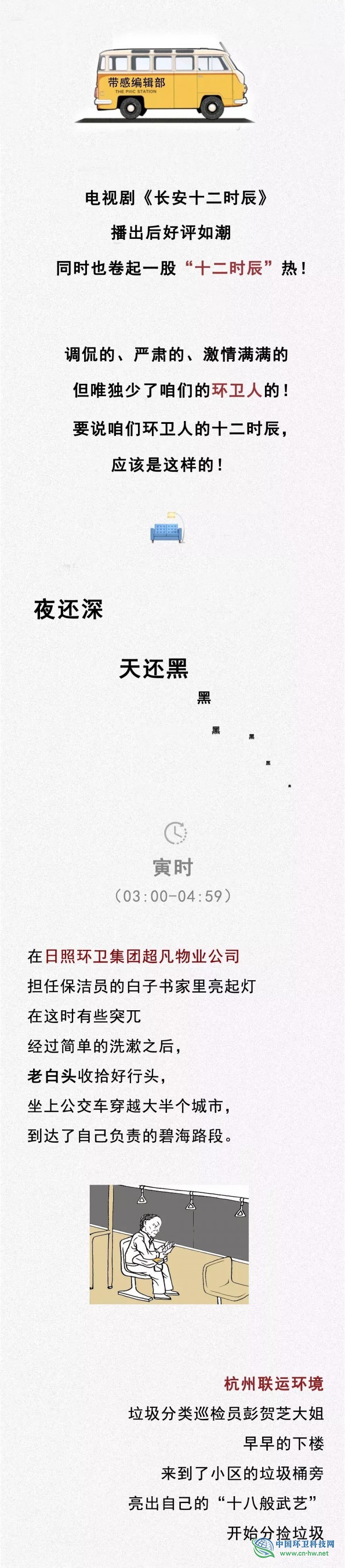

 “邻避”堡垒松动 垃圾焚烧发电进入高质量成长期
“邻避”堡垒松动 垃圾焚烧发电进入高质量成长期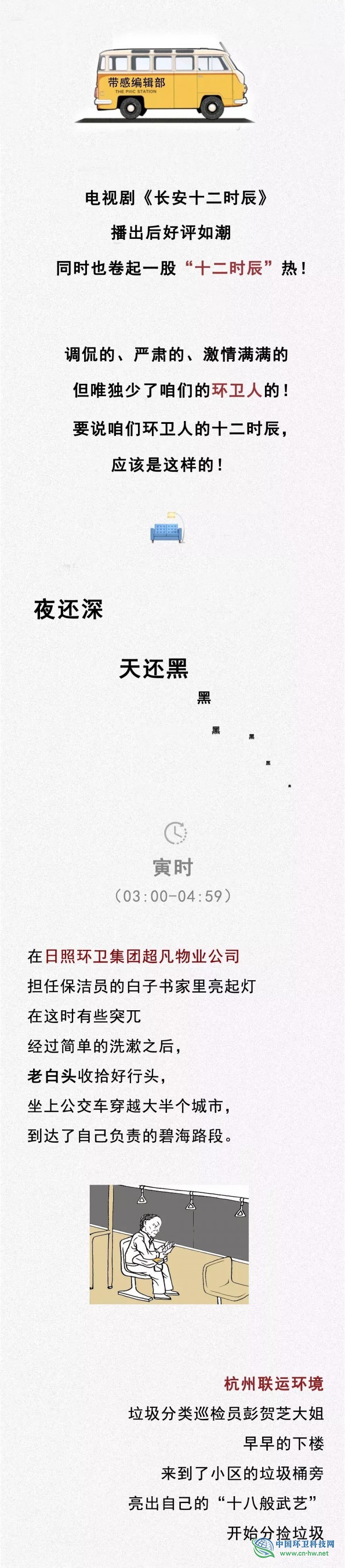 环卫人的12时辰!
环卫人的12时辰!
 环卫科技网公众号
环卫科技网公众号 乐分圈微信公众号
乐分圈微信公众号 厕重点微信公众号
厕重点微信公众号 环卫装备微信公众号
环卫装备微信公众号
 关闭
关闭 关闭
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