赔偿程序启动时距离事件发生已近1年,为了核实生产的真实性,政府要求农户提供当时的电费发票。刘玉成和胡玉虎没有从事养殖,自然拿不出发票。后来,他们找到张家街道水产站站长刘辉,说“如果得到赔偿,这个钱我们不会自己花”。刘辉就明白是什么意思了,告诉他们写一个说明,写明用的是柴油机发电,没有使用国家电网的电,这样就不用出示用电发票。然后,刘辉召开了村水产养殖户会议和村水产专干会议,要求我们把所有材料都提供给街道。张家街道公示日期是2011年7月15日,但8月19日刘辉伪造了一张公示赔偿的表格,并伪造了街道办刘副主任的签字,让我和村支部书记一起签字盖章,证明这两户通过了村委审核。2011年12月份,赔偿款发下来,这两户也拿到了赔偿款,一共是1140936元(访谈编号:DL2015041303)。
确实如他们所说,“这钱不会自己花”,当地《人民检察院讯问犯罪嫌疑人笔录》中记录了刘辉的原话:“我确实不知道谁家没有养(殖),就是公示4次,每次7天……当公示完了以后,钱都发下去了,刘玉成先过来给我拿了5万元钱,在这之前给我拿了海参,过了几天胡玉虎也给我拿了5万元钱”。而刘辉也意识到他们送钱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确实没有养殖,拿不出有效的应获得赔偿的证明依据,但我依然给他们通过审核并向新区海洋渔业局申报了,才使他们获得了赔偿款,他们事后为了表示对我的感谢,所以送给我钱”。后来,大连市人民法院以刘辉收受贿赂罪和滥用职权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1年。
2013年1月30日的《人民检察院的讯问笔录》相关材料为抗争精英老赵提供的复印件(2015年4月调查资料)。记录了刘玉成的造假过程,再现了其谋利过程。
2004年年初,我和刘靖(侄子)以及刘玉平(弟弟)投资了100多万元,建成了育苗室,我为法人代表。从2004年底至2008年初,我们先后养殖了海参苗、虾夷贝这么几茬。由于水质不好,加之后期价钱不好,我们的投入全部亏损,另外还亏损了100多万元。到2008年年底的时候,我们就不干了。直到2010年7月16日,溢油事件发生,当时我们的育苗室并没有实际生产。过了一个月左右,海面浮筏、海底养殖、滩涂养殖还有育苗室的养殖户都在传言国家要给溢油补偿,不记得是街道还是赵村好像在调查摸底我们的损失。赵村有6、7家育苗室,李飞和刘大发的老婆召集我们家的刘靖等几家养殖户制作损害赔偿的申报材料,并且还去北京上访(着重号为作者添加)。到2011年5、6月,赵村或张家街道水产站传达了市政府给养殖户溢油补贴的政策后,我就向街道水产站提供了虚假的供电说明、虚假的《辽宁省水产苗种生产、用药、销售记录》、营业执照复印件及生产许可证等补偿需要的证明材料,后来街道和村里就来人测量水体,之后进行公示,到最后我得到了50多万元的补偿款。
刘玉成的《笔录》清楚地表明,他在溢油污染发生的2年前就不再从事育苗养殖。但当听说可能获得油污赔偿款时,他做了这样几件事:一是“制作损害赔偿的申报材料”——毫无疑问,这种损害材料是虚假的;二是提供虚假证明材料,包括供电说明以及生产、用药和销售记录等;三是向街道水产站负责人行贿;四是参加了到北京的上访活动。刘玉成的侄子刘靖在《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检察院讯问笔录》中谈到了他们的上访心态:“‘7•16’补偿这件事,从一开始我就是跟着别人走。我和他们一起上访就是为了获得赔偿款,如果国家不给就拉倒”。可见,正是经济利益的刺激,让他们加入到了谋利型抗争队列之中。
除此之外,还有不少养殖户通过多报和谎报养殖面积的方式谋利。在这方面,拥有社会资本、与基层政府水产部门有利益关联的人,具有更多的谋利资源。“胆大者谎报养殖面积,得到的赔偿款就多;胆小者如实上报,得到的赔偿款就少。比如,有的人实际养殖面积是80亩,登记时依然为80亩,但有些养殖80亩的却登记成200亩。再比如,有的养殖户只有100台筏子,听说要赔偿时就偷偷地再打100台筏,然后和村干部搞好关系,让村干部报200台筏,国家给钱了就给他们分点”(访谈编号:DL2015041106,DL2015041107)。
在农村的熟人社会,村民们即使不了解其他养殖户的准确养殖面积,但也知道大致情况。面对其他村民的谋利现象,获得赔偿较少的养殖户心理不平衡,对谎报和虚报面积以及暗箱操作行为开展了举报和上访。地方政府倍感压力,于是启动了损失复查工作。随后,谋利者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不但补偿款被收缴,还以涉嫌骗取国家资金罪逮捕和判刑(基本都是缓期执行)。对基层政府而言,之前面临的信访特别是进京信访的压力很大,而此次采取的“消访”举措无疑是釜底抽薪式的,后来再没有发生源自赔偿诉求的大规模上访。













 盈峰环境排水抢险车赴
盈峰环境排水抢险车赴 2020全国厨余(餐厨)
2020全国厨余(餐厨)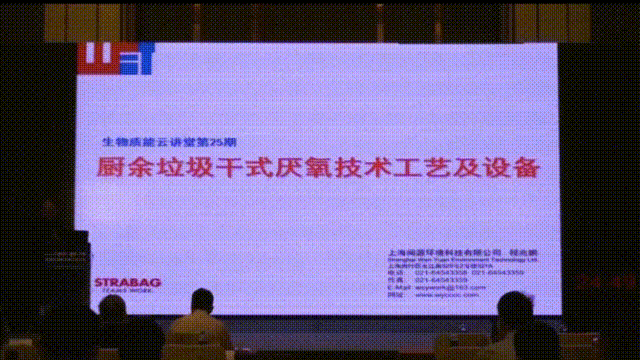 2020全国厨余(餐厨)
2020全国厨余(餐厨)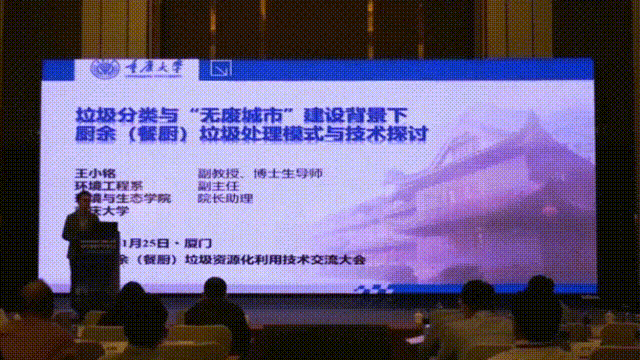 2020全国厨余(餐厨)
2020全国厨余(餐厨)
 环卫科技网公众号
环卫科技网公众号 环卫微学院公众号
环卫微学院公众号 乐分圈微信公众号
乐分圈微信公众号 厕重点微信公众号
厕重点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