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经济建设应考虑村民的消费意愿
乡村建设要高度重视外力救济乡村,高度重视经济建设,尤其要优先建设县级农村工业园和强化乡村保障,让村民“有钱花”和“敢花钱”。之所以强调优先推动县级农村工业园建设和乡村保障体系建设,是因为这些建设项目让村民资产保值和增殖,自然会受到村民欢迎、拥护和珍惜。不妨把这类让村民资产(或更大范围的财产)增殖的经济建设称为“增殖性经济建设”;相应的,那些向村民收费因而减少村民资产的经济建设可称为“消费性经济建设”,如农村房屋改造、污水处理等项目。消费性经济建设是村民的负担,甚至超过了村民的承受能力,如在仍有部分村民不愿购买医保的乡村推进,遭到村民抗拒便不足为奇。
“村民上楼工程”和“农村污水集中处理工程”是2个村民较抗拒的事例。上马村民上楼工程是为了整治陈旧、破败村容村貌、美化村庄和改善村民居住条件(个别地方也可能还为了土地置换);农村污水处理工程是为了解决污水横流、臭气熏天问题,按理讲应受到村民欢迎,但忘了考虑村民的经济条件和消费意愿,即是否“愿花钱”购买服务。
总的讲,乡村经济基础较薄弱,村民消费意愿较低。乡村经济具有三大特点:一是农民收入偏低,2019年农民人均可支配年收入16021元,农民人均消费年支出13328元;二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家庭经营性收入(2019年占比33.5%)和工资性收入(2019年占比40.6%左右)需看天看老板,存在不稳定风险(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较稳定,但只占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5.9%);三是用于居住和污水垃圾处理等生活服务的支出比例一般不超过消费支出的25%,以2019年农民人均消费支出13328万元计算即人均年支出3330元。
以五口之家计算,村民住进一栋占地100平方米的三层半房屋,至少得花费42万元,即使采取20年按揭方式购买,每年需支付1.68万元以上,人均居住支出3360元;又如农村污水集中处理,一些地区提倡打包PPP,增大了管网建设费用,致使污水处理设施及其配套管网建设成本飙升到人均1200多元以上,人均年支出达150元以上(每立方米污水收费高达4元/立方米以上);人均居住和购买污水处理服务的年支出为3510元,超出了人均年支出3330元的支付意愿。如果家庭人口较少,人均支出压力将更大,如四口之家的人均居住和购买污水处理服务的年支出将升高到4350元,有可能超出家庭承担能力。
这里围绕村民资产增殖和消费,涉及到了乡村建设的三个方面,也是乡村建设常遇到的三个问题,从中可挑明乡村建设好坏的判断标准。概括如下:
(1)增殖与消费的关系问题,通俗讲,即“有钱花”“敢花钱”“愿花钱”之间的关系问题。要优先上马增殖性经济建设项目,让村民有钱花和敢花钱。要在村民“有钱花”“敢花钱”基础上才上马消费性经济建设项目,而且,制定融投资模式、建设模式和收费标准时必须考虑村民的消费意愿和经济承担能力,即使像新农合医疗保险类等乡村社会保障项目也应根据村民的消费意愿和承担能力制定缴费标准。
(2)面子工程与精打细算的关系问题。救济乡村其实是城市救济乡村和城里人(企业家、知识分子、机关团体等)救济乡村,带点城市色彩和搞点“面子”形象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始终要记住,救济的对象是需要外力救济的乡村及其村民,需要因地制宜和精打细算,搞出的东西要具有乡村气质和为村民认可,不能移植城市那一套,如在纯农业地区建设大型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只会落个“吃力不讨好”的烂尾结局。一些人移植城市的生财之道,耍奸商逻辑,把小事搞成大工程,图谋从乡村那里挣横财,这就是不厚道了。
(3)“止病痛”与“治病根”的关系问题。乡村存在“贫、愚、弱、私”等问题,更存在“愈贫、愈愚、愈弱、愈私;愈私、愈弱、愈愚、愈贫……”般金钱、智力、权势和境界之间的因果相循;相应的,乡村建设也存在两种取向。取向一是只看到乡村问题,用西医疗法来“止痛”,如送钱、建房、建污水垃圾处理设施等,即授之以鱼;这种建设见效快,表面好看,但不持久且不能根本解决乡村问题,甚至加重乡村的负担。取向二是用中医方法斩断金钱、智力、权势和境界之间的因果相循,根据病因来安排乡村建设,授之以渔,提高乡村的自我造血功能,县级农村工业园建设和乡村保障建设就属于这种取向,本来是要解决乡村问题,却先解决就业与保障等人的问题。
3.5三治并举
三治(自治、法治、德治)并存于乡村。乡村自治是让村民自我管理;乡村是村民的社会,村民是乡村建设的主力和主体,提倡乡村自治顺理成章;而且,中国乡村有着自治的传统和理性,有能力施行自治。乡村德治是让伦理道德统治乡村;乡村仍是伦理本位,讲究伦理道德;而且,传统的伦理道德中存在积极东西,与新时代“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相容,提倡德治也顺理成章。法治是让法律及相关的制度统治乡村;法治是现代国家和社会的标志,是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之一,培养村民的公民精神离不开法治,理当强化乡村的法治。三治是乡村建设的三种方法、手段和工具,也是乡村建设的三个目标,乡村建设应通过三治并举促进三治融合。
乡村自治是自汉朝以来的各朝各代普遍施行的地方治理模式,不仅仅是乡村治理的一种传统,更是中国乡村的一种理性,重在建设美好乡村。中国村民天生下来便有自我约束以求乡村有序和谐的理性,虽说皇权无远弗届,但山高皇帝远,中央政权乐于采用“皇权不下县”来平衡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官府只管地方财税、军队和意识形态等大事,把一些具体事务的管理权交给地方自决,一方面节省了资源,降低了管理成本和提高了统治效率,另一方面提高了地方自我管理能力,形成了地方自治的理性。地方自治,尤其乡村自治和社区自治,符合现代化建设的需求,应当发扬光大。
当下的乡村自治主要是村自治(乡镇是一级政府,行使公权力),自治组织是村民委员会(村委)。乡村自治是围绕乡村的人和事的管理和服务。首要是人的管理、服务和教育,催人向上;中国最早的成文乡约《吕氏乡约》(公元1076年)要求“德业相劝”“过失相规”,便是着眼于人生向上。其次,是日常事务的管理和服务,主要的日常事务有生产管理、社会保障、市场监督、健康卫生、环境卫生、治安消防、便民服务和财务会计等。当下的乡村自治偏重于日常事务而忽视顶级重要的人,在日常事务中又忽视了非常重要的生产,这是“抓了芝麻,丢了西瓜——划不来”。不把生产搞上去,不把人教育好,哪里会有美好乡村,这样的乡村自治不可能有活力和生命力。
德治是中国社会早熟的象征,重在维持人与人、事、物的有序和谐关系。德治的历史长于乡村自治历史,自有中华民族便有德治,至少可以肯定地讲,自公元前500年前后轴心时代起,中国乡村便确立了德治。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是一部德治史,中国乡村是个仁义道德社会,德治深耕人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幸福观。三纲五常,亲亲齐物,克己复礼,修齐治平,顺时应物,与世为善,天人合一,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及慎权、慎独、慎微、慎友,道德内在,良知天理等,这些伦理道德是心是情是理也是主宰,“惟德动天,无远弗届,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平衡了人与人、事、物之间的关系,充分证明了道德在凝心聚力、净化风气、维护稳定等方面的引领和激励作用。
当下乡村不仅不能丢弃伦理道德,更要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加强信用体系(平台)建设,强化为人处世的底线思维,形成公民道德建设合力,充分发挥道德的力量。独处时自觉实行自我监督,“吾日三省吾身”“心存敬畏,手握戒尺”;群处时坚持道德标准,正确处理个人与家庭、社会、国家和自然的关系,尤其要打造良好的家风,把对家庭的小爱转化为对国家的大爱,传递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俭持家、邻里团结的观念,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寓己于民族复兴,为民族复兴打下坚实的伦理道德理性。要持续推进美丽庭院打造、垃圾分类、文明出行、文明家庭评选等专项活动,发挥典型的带动作用,进一步增强乡村的道德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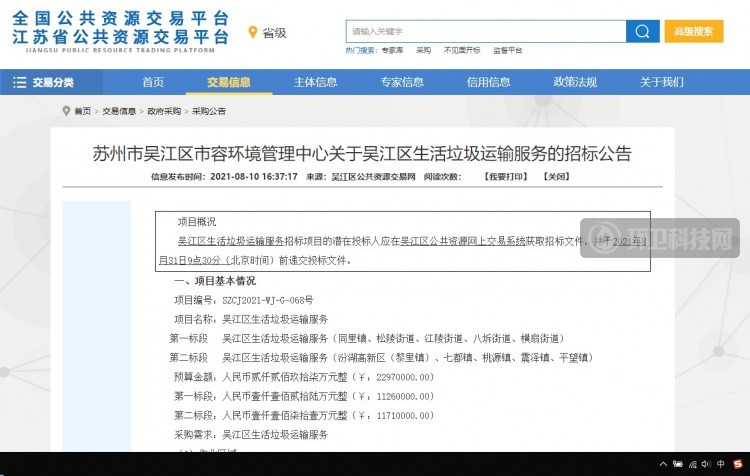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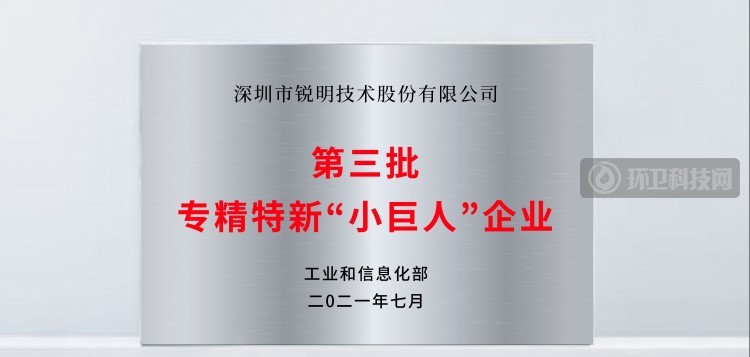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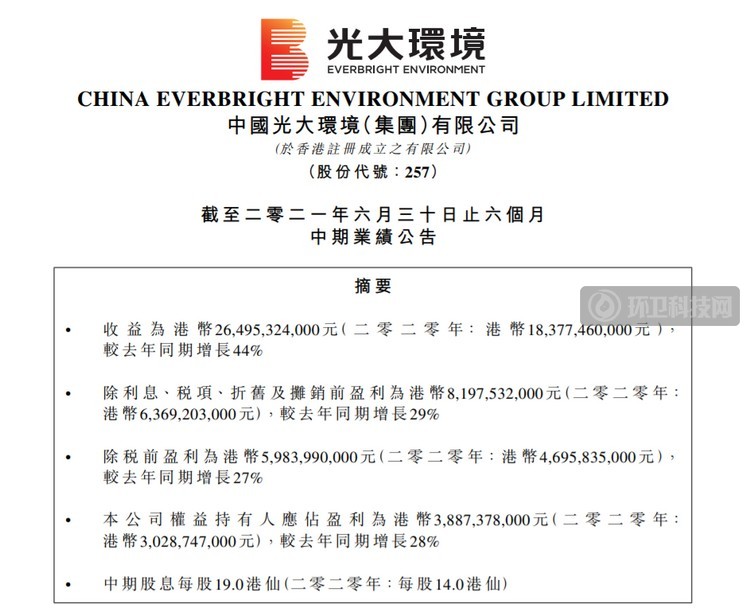

 盈峰环境排水抢险车赴
盈峰环境排水抢险车赴 2020全国厨余(餐厨)
2020全国厨余(餐厨) 2020全国厨余(餐厨)
2020全国厨余(餐厨) 2020全国厨余(餐厨)
2020全国厨余(餐厨)
 环卫科技网公众号
环卫科技网公众号 环卫微学院公众号
环卫微学院公众号 乐分圈微信公众号
乐分圈微信公众号 厕重点微信公众号
厕重点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