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2中国当代乡村社会保障的演变
谈及中国当代乡村社会保障,必须介绍几个时间节点的重大决策。一是1953年开始实施粮食统购统销,1958年人民公社化、开征农业税和建立户籍制度,为开展农村集体保障奠定了基础,也埋下了城乡发展失衡的祸根。
二是1982年中央1号文认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强化了土地与家庭在乡村社会保障中的作用。1984年中央1号文正式规定并允许基层统筹,为农村以“三提留五统筹”自积累手段解决乡村社会保障铺平了道路。
三是2002年、2007年和2009年先后出台有关实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文件,2005年底出台取消农业税的政策,为建设现代乡村社会保障体系奠定了基础。
从上可见,当代乡村社会保障大体可分为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末和21世纪以来2个阶段。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末,乡村社会保障处于农村集体保障和社会救济辅以政府救济的较低层次,资金筹措以基层提留统筹为主,主要工作限于合作医疗、教育、五保供养、军人优抚、救灾、扶贫开发等内容。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强化了土地的保障作用,但未提高乡村社会保障的层次。1993年后,乡村社会保障在养老、新型合作医疗等方面进行了试点,乡村社会保障的改革明显滞后于城市社会保障的改革。
进入21世纪以来,现代乡村社会保障体系加速成形。该体系以政府、集体、社会和个人为主体,多渠道筹资,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和农民社会养老保险为基础,进一步完善五保供养、救灾、扶贫等救济和优抚安置制度,扎实推进农民工参与社会保险、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医疗救助和教育救助等工作,同时取消农业税(自2006年1月1日起)、完善农业生产“四补贴”和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顶托农业生产。2003年可称为中国的现代乡村社会保障元年。
2.3.3中国当代乡村社会保障的主要困难
(1)乡村社会保障的传统模式影响深远
传统上,中国乡村社会保障实行的是一种土地保障辅以亲疏厚薄差序“小圈子”保障的模式,一种靠土地保从容、赖差序格局度艰难的模式。在这种传统模式下,每个人力求自给自足和自保自救,而当自身力量不济时,优先求救于家庭(户)、家族和亲属提供的血缘保障,其次求救于邻里朋友提供的地域保障,不到走投无路绝不会求救于政府提供的政府保障——政府救济和优抚安置。
这种传统模式的形成是由中国乡村社会的乡土性和差序格局决定的。乡村社会的乡土性决定土地不仅是一种生产资料,也是一种基本生活保障,时至今日仍然如此。2018年乡村调查数据表明,80%受访者视土地为生活保障,41%视土地为收入保障,21%视土地为养老保障,另有20%把土地视作精神寄托。乡村社会的差序格局决定,当遇到天灾人祸以致土地无法保障从容与平安时,村民会自发地依托自己的差序格局自救,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传统的由血缘保障、地域保障和政府保障组成的差序保障方式。
但这种传统模式是一种可靠性较差的保障模式。首先,传统模式淡化政府保障的作用,立足自保自救,且置村民基本生产生活保障于土地,而这种土地保障本身又受天时地利人和的极大影响,具有不可预见性,换言之,土地保障本身便需要更可靠的保障。其次,差序保障方式更多的是一种道义上熟人共度艰难的社会救助方式,且家庭(户)和政府外的保障大多是基于“好借好还”契约的一种民间借贷关系,一方面较难确定熟人在困难时刻是否可以提供、能够提供多少救助及允许多长缓冲期,即较难确定借贷的易得性、可预期性和有效性,另一方面,阻碍借贷双方事后的从容发展,甚至因“一人受困,众人为难”导致困难蔓延局面,此外,有可能引起民间借贷纠纷和高利贷事件,破坏邻里和谐。正因为传统模式的可靠性较差,使得村民有钱不敢花,从而阻碍了乡村资金的流转或社会化,不利于乡村建设。
即使如此,这种传统模式可谓历史悠久、盛行千年且影响深远,甚至由乡村波及城市,原因就在于它是由下而上自发产生,根植于每个中国人血液里流淌的文化基因。可以断言,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乡村社会很难扬弃其基于血液、地缘的归属感及由此建立的差序格局,也就很难扬弃“求人不如求己”“远亲不如近邻”“远水救不了近火”等观念,乡村社会保障的传统模式就仍有生命力。如何妥善处理传统与现代乡村社会保障模式的关系,使其相互对接和相容相生,让乡村社会保障更可靠,是一个值得重视的课题。
(2)乡村社会保障的社会化能力弱
现代乡村社会保障的历史短。中国直到1986年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提出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概念;在1993年第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议》才将社会保障界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五大支柱之一,才明确社会保障体系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安置和社会互助、个人储蓄积累。
1993年后,城市社会保障的改革工作迅速展开,在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和住房等方面取得巨大进展,建立健全了“五险一金”制度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新型社会保障制度,形成了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安置和社会互助共存的城市社会保障体系。但同时期的乡村社会保障的改革相对滞后,处于先行先试阶段,具体工作仅限于救济和优抚安置性质的五保供养、农村救灾、扶贫开发和试验性质的合作医疗试点等。
进入21世纪以来,现代乡村社会保障体系才加速成形,该体系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2003年始)、最低生活保障(2007年始)和农民社会养老保险(2009年始)为基础,进一步完善五保供养、救灾、扶贫等救济和优抚安置制度,扎实推进农民工参与社会保险、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医疗救助和教育救助等工作,同时取消农业税(自2006年1月1日起)、完善农业生产“四补贴”和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顶托农业生产。2003年是中国的现代乡村社会保障元年。
乡村社会保障的社会化能力弱。村民参保意愿和社会资本投资意愿都较小,导致乡村社会保障的社会化能力较弱。村民的参保意愿不高和个人缴费比例偏低,如2017年各地农村新型合作医疗的个人缴费与政府补贴之比普遍低于1:3,个别地区甚至低于1:8,除传统的亲疏差序保障观念等影响外,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低和收入来源不稳定,即村民的经济承担能力小是关键原因。2017年村民收支情况是,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432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6396元),村民人均消费支出10955元(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24445元),村民人均剩余仅2477元(城镇居民人均剩余11951元),村民的收支及剩余都偏低;而且,村民收入主要来自家庭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2017年,家庭经营性收入42%,工资性收入51%),农业收入“看天吃饭”,外出务工“看市场吃饭”,村民收入存在不稳定风险。
此外,社会资本投资意愿较小。因乡村公共服务基础设施、服务功能和服务队伍建设等不完善,可用资源不足,再加上村民的经济、社会、文化等背景降低投资收益、增大服务难度和投资风险,导致乡村对服务人才和社会资本的吸引力较小,后果是乡村创业创新动力不足、企业数量质量偏低、集体经济薄弱和公益慈善事业落后,村民难以享受集体分红、企业年金、社会保险、慈善服务等来自社会的保障。
总体上,与城市社会保障改革比较,乡村社会保障改革相对滞后,乡村社会保障的社会化能力较弱,资金缺口较大,乡村社会保障的政策、制度和体系有待完善,乡村社会保障是中国社会保障和市场经济体制的短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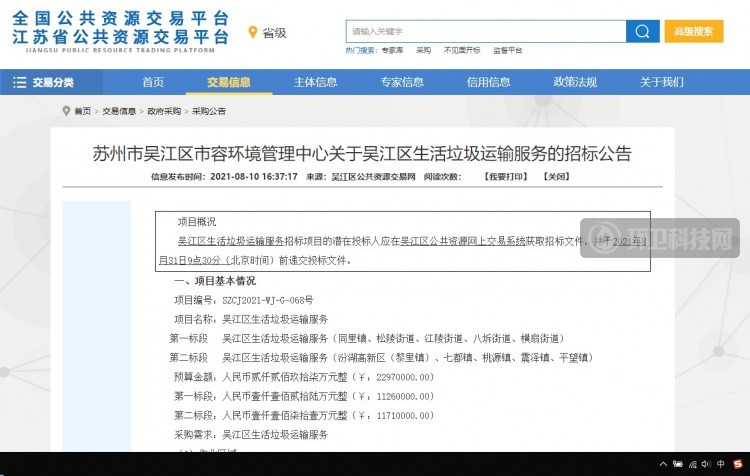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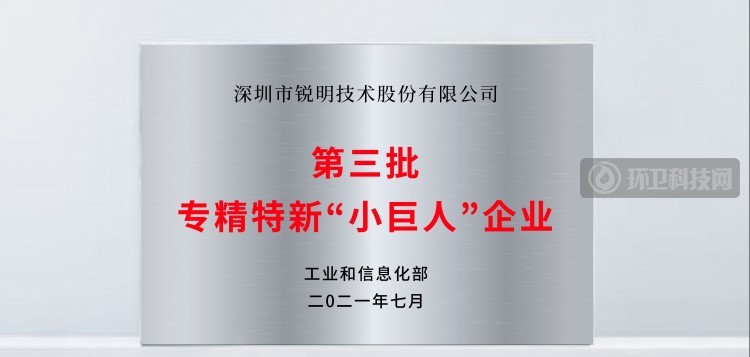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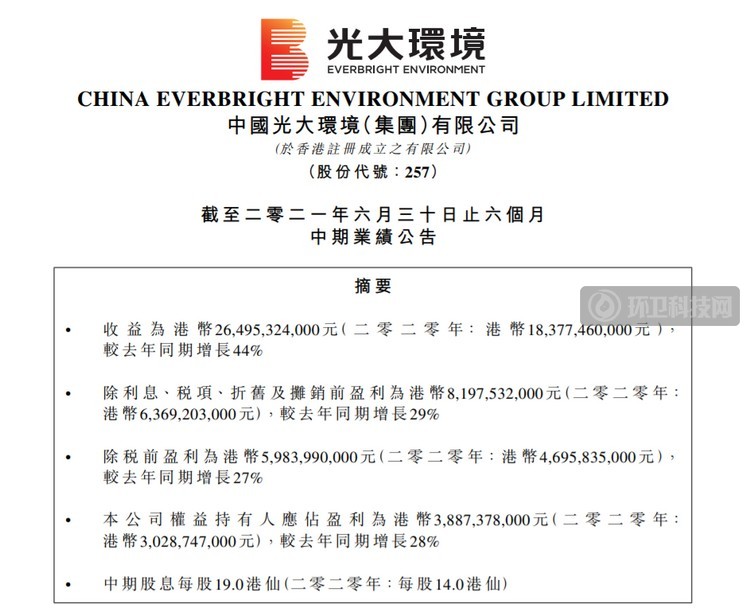

 盈峰环境排水抢险车赴
盈峰环境排水抢险车赴 2020全国厨余(餐厨)
2020全国厨余(餐厨) 2020全国厨余(餐厨)
2020全国厨余(餐厨) 2020全国厨余(餐厨)
2020全国厨余(餐厨)
 环卫科技网公众号
环卫科技网公众号 环卫微学院公众号
环卫微学院公众号 乐分圈微信公众号
乐分圈微信公众号 厕重点微信公众号
厕重点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