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北京为例,北京市于2009年率先在朝阳区麦子店社区、海淀区鑫泰大厦两个社会单位开始试点垃圾计量收费。探索社会单位垃圾排放收模式,按照“谁生产谁付费、多生产多付费”的原则,并逐步由生活垃圾单一定额或议价收费,过渡到计量收费。另据相关报道,北京市将启动市属垃圾处理双向称重和实时统计,启动垃圾处理刷卡收费系统建设,并核定各区县垃圾产生量和进入市属设施处理量,实施超量加价措施,今后超量排放垃圾将提高收费费率。另外,杭州、上海、广州等地已经在酝酿实施垃圾计量收费。
2.计量收费的定价标准。对于制订城市生活垃圾计量收费的定价标准,要着重考虑以下几方面因素:首先,要充分考虑垃圾处理的成本。对于垃圾处理厂商而言,垃圾收费是其总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要使计量收费得以顺利实施,单位定价问题是不可忽略的。从根本上来讲,定价的出发点是垃圾的处理成本。定价高低会直接影响到垃圾处理者的收入。在市场机制下,垃圾处理厂商的利润至少应与其他部门的平均利润相等。如果利润过低,会导致垃圾处理厂商退出市场,使垃圾得不到有效处理,从而导致垃圾的堆积和环境污染。利润过高又会导致过多的厂商蜂拥而入,破坏了垃圾处理产业的正常秩序,也不利于垃圾处理产业的健康发展。[6]其次,要兼顾各地的经济状况和居民的收入水平。如果定价过高,会影响企业的利润和居民缴费的积极性,更甚者可能导致引发“非法倾倒”的现象;若定价过低,又难以弥补垃圾处理的成本,难以引起人们对垃圾减量化和资源化的重视。再次,要在现行的垃圾处理收费标准的基础上,适当提高垃圾处理及费用标准,鼓励市民和社会单位从源头上实施垃圾分类和垃圾减量。均等定额收费模式向计量收费模式的转变,并不是一蹴而就的。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配套基础设施的建设、对居民的宣传教育等方面都是计量收费模式得以实施的助推器。配套基础设施既包括计量工具的配备,也包括垃圾处理设备、垃圾回收系统的建设,这都需要漫长的过程。
基于此,笔者认为,在收费模式转变的过程中,可以根据不同阶段、不同地域的情况采取不同的进度,在发达的城市社区实行垃圾计量收费制,在欠发达的地区和配套设施不完备的城市社区可先采取定额收费制,等条件逐渐成熟后再完成定额收费向计量收费模式的过渡。
(三)多渠道并行确保垃圾处置费的收缴,建立严格的垃圾处理费管理体系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收缴困难以及费用管理和使用上的漏洞,会直接导致城市生活垃圾收费制度形同虚设。据统计,中国自实施垃圾处理收费制度以来,每年的平均收缴率仅在30%左右。即使在广东等垃圾处理费收缴率较高的城市,按现行的征收标准足额征收,所收缴的垃圾处理费也仅能补偿垃圾处理运行成本的40%左右。[8]因此,要充分利用信贷等多种渠道解决垃圾处理费收缴难的问题。在征收途径上,可将垃圾处理费附征于水、电、煤气等人们日常生活必需品的收费项目中,以此敦促人们按时足额的缴纳垃圾处理费。
另外,可将垃圾处理费的缴纳情况纳入到个人银行贷款信誉评价体系中。如居民逾期不缴纳垃圾处理费,将直接影响到其在银行贷款的信用。配套设施发达的城市还可采用缴费卡与个人信用卡联网的方式。如居民逾期不缴纳垃圾处理费,银行将自动从其银行账户上划拨相关费用。对于征收来的城市垃圾处理费,应专项用于城市垃圾集中处理设施的运营、维护和项目建设。实践中,对收缴的垃圾处理费需要建立严格的管理体系,确保各环节的公正透明,将费用专款专用于城市生活垃圾的处理。
各城市征收的垃圾处理费应当单独设立账户,专款用于城市生活垃圾集中处理设施的建设、运营和维护。对尚未建成城市垃圾集中处理设施的城市所征收的垃圾处理费,可用于垃圾处理工程的前期工作和相关配套项目的投入。既要防止负责征收部门的擅自留用,又要防止将垃圾处理费挪作他用。垃圾处理费的征收部门要对其使用情况实行信息公开,接受公众监督,听取公众意见。指定专门部门对垃圾处理费进行管理,对将费用擅自留用或挪作他用的单位或个人追究法律责任。鼓励公众参与垃圾处理费的管理和监督,并实行相应的奖励机制。对检举垃圾处理费用管理过程中违法行为的个人,可免收或减收垃圾处理费。
(四)责任追究机制应更加严格和规范
虽然相关部门对生活垃圾收费的必要性做了肯定,并通过部门规章对生活垃圾收费的内容作出了规定,但具体的实施细则并不详细。特别是对法律责任的规定,存在责任主体不明确、范围过窄,责任内容不明确、不全面,处罚措施力度不够等诸多缺陷。笔者认为要完善如下几方面的规定:
1.明确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的实施是从源头上促进垃圾减量化和资源化的重要途径。其概念是在1988年由瑞典的环境经济学家托马斯给瑞典环境署提交的一份报告中首次提出的。是指以生产者为主导的责任主体对消费及其它环节所产生的废弃物的回收、循环利用和最终处理所应承担的责任。[9]我国2008年颁布的该法规定“生产列入强制回收名录的产品或者包装物的企业,必须对废弃的产品或者包装物负责回收”。然而,《循环经济促进法》虽规定了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强调了生产者的回收责任,但并没有对生产者违反产品回收义务后所应担负的法律责任做出规定。缺乏法律责任的追究机制必然会致使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的实施效果大打折扣,因没有执行力,而无法达到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效果。法律责任的设置不仅从客观上对责任者起到震慑和监督作用,更是为公众提供法律救济的依据。因此,相关法律需要健全和完善,需要进一步明确生产者在违反回收义务时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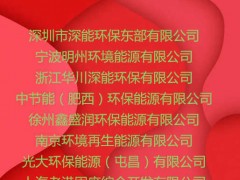






 山东省东营市0001号垃圾分类绿色小屋揭牌!
山东省东营市0001号垃圾分类绿色小屋揭牌! 又是渗滤液!垃圾填埋场渗滤液问题整改不到位被约谈
又是渗滤液!垃圾填埋场渗滤液问题整改不到位被约谈
 环卫科技网公众号
环卫科技网公众号 环卫微学院公众号
环卫微学院公众号 乐分圈微信公众号
乐分圈微信公众号 厕重点微信公众号
厕重点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