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另一方面我们要看到,这是一个文明化的过程,厕所问题实际上需要在城市化、工业化下系统性地解决,而不是归咎于个人的文明素质或者谁不讲卫生的问题,它需要社会体系的成长。中国在1964年前后,北京胡同里还需要掏粪工,这是我们社会分工的一部分,而不能简单地说它是落后的或者坏的,这并不意味着文化的优劣。随着都市化的成长,国家才能通过程式化的方式大规模建立有效率、合理的、经济的下水道系统,而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当然比较先行。
中国现在的社会状况相当于三四十年前的日本,日本与中国的厕所革命进程非常相似,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在上世纪70年代,日本的经济高速增长,基本实现现代化。但是在60年代以前,日本的厕所跟中国基本上一样,比如说农村的农民会把城市居民的粪便拿回去做肥料,一开始得拿点农副产品,拿着蔬菜和城里人换,形成固定的交易关系。但是工业化到一定程度,农民开始用化肥的时候,没有人愿意掏粪了,就一下颠倒过来,城市居民巴不得你赶紧来,甚至我付你钱,让你把粪便运走。而日本的高度现代化的下水道系统是在60年代才慢慢建立起来,到70年代才完善,但依然还有很多偏僻的地方没有建立。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工业化、城市化与社会文明协调发展的结果。从厕所这个侧面,可以看出中国文明的成长。中国已经成为经济大国,到了这个时候,厕所革命现在成为一个问题,也成为了我们的使命。只有让人们拥有文明的、有尊严的、舒适的排泄的环境,你才能说现在是一个现代文明的社会。
关键是学术界关注更多的是优雅的部分,对上半身关注的多,对下半身关注少,几乎没人关注。我的人类学同行和社会学同行里没有人做(相关研究),那把它做出来就是我的责任。学术界对中国社会当下面临的问题,应该有一个基本的关照。在这本书里,我试图阐释应该如何理解中国的厕所革命,我基本的判断是,厕所问题是中国人想要更好地获得幸福感绕不开的事情。
界面文化:你的书中有很大篇幅在叙述中国厕所革命的进程,你觉得它起步的节点是什么时候?它主要的动力又是什么?
周星:动力首先是来自外部的压力和外部的凝视,我们变成外人的他者,我们被讲述。另一方面是我们自己的生活在变革,中国大陆现在的厕所革命源于一个更宽泛视角下的生活革命。中国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连续4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导致中国人民的生活品质极大提升,衣食住行都发生极大变化,所以我用“生活革命”这个词。厕所革命这个词最早还不是人类学家提出,而是当时中国建设部搞建筑设计的人提出的。中国老百姓家里的厕所原来是在胡同或四合院里,厕所是公用的。现在一个单元房里要怎么配置厕所,多大的面积是合适的,背后有一个复杂的考量。过去的中国搞民间传统建筑的设计师们不会考虑这些问题,但是要设计现代工业化、大批量建造的单元楼建筑,就绕不开厕所的设计。
另外,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特别穷,没有外汇,靠旅游业吸引外国游客消费,挣点外汇,有外汇我们才能维持基本的国际交流。外宾对我们什么都满意,就厕所不满意,你要查那几年的《参考消息》,关于厕所的抱怨特别多。所以旅游局逼着地方政府,把各个景点的厕所搞好,让观光客的旅游体验更好,所以你也就能理解,为什么现在旅游局在主导中国厕所革命,就因为有这个传统。这个变化确实有一个外因,但是内在的动机还是更根本的。一开始我们是被动的,但是到了到21世纪初,国家领导人都重视这个话题,就是因为我们内在的需要:我们已经不是为了外国人舒服,是为自己舒服。我们动机已经变了,这是中国社会一个跨越式的成长。
当然,如果说最早的起源,要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的“新生活运动”,延续到建国后的“爱国卫生运动”,那时候我们要摆脱“东亚病夫”的名字,就要把卫生搞好,厕所的管理与清洁就是其中的一部分。但是那个时候是为了搞卫生,现在我们认为人在排泄的时候还是需要尊严感与舒适感的,这种感觉跟过去不完全一样。
界面文化:我们大家都知道在改革开放之前,政府对于人的生活是更全面管制的,可是那时候没有对公共厕所进行非常有效的现代化改造,为什么到改革开放之后政府反而更关心“厕所革命”呢?
周星:我觉得和人口流动有关,过去公共厕所没有那么重要,那时公厕数量少,但流动人口也特别少。虽然人不方便,但是并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改革开放以后最大的变化就是社会全面流动起来,过去的公厕就是在公园有一个,去公园的都是周围市民,农民根本就不进城。人口流动也来自体量庞大的国内旅游业和国际旅游业,游客的体验起到了很大的影响。他吃、住、行、玩都还不错,最后厕所不好,前面的印象就打折扣,过去是国际游客不满,现在是国内游客在投诉。为什么投诉?我们人民也跟过去不一样,人民知道了好的厕所是什么样子。以前家里是蹲坑,所以公厕也是蹲坑,没什么区别,但现在人家里是抽水马桶!还有一个原因是政府认知的变化,中国政府是学习型的政府,正在学习管理一个现代的、人口高速流动的社会。
人民的公共性随着公共厕所的开放与增多而成长
界面文化:你在书中提到,公共厕所反映的是大众对公共空间的认知,现在厕所革命不断推进,是不是意味着中国大众的公共性发生了改变,更愿意共享与维护公共空间?但为什么同时城市存在大量的封闭的小区,你如何看待中间的矛盾?
周星:中国社会在这点上,还不是一个成熟、开放的公民社会。还是以公共厕所作为例子,出于安全或管理的考虑,中国社会很多小区、机关单位和学校都不会开放自己内部的厕所。比如说一个内急的人在长安街上找厕所,他就没办法找到。大家都会谴责随地大小便的人,但社会没有为他提供好的公共厕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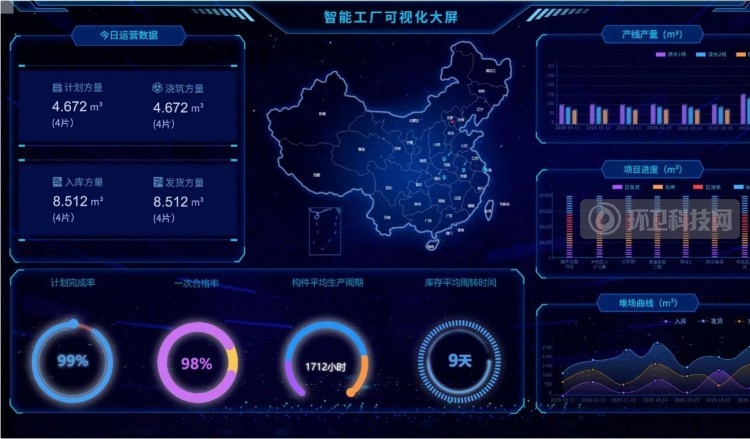


 盈峰环境排水抢险车赴
盈峰环境排水抢险车赴 2020全国厨余(餐厨)
2020全国厨余(餐厨) 2020全国厨余(餐厨)
2020全国厨余(餐厨) 2020全国厨余(餐厨)
2020全国厨余(餐厨)
 环卫科技网公众号
环卫科技网公众号 环卫微学院公众号
环卫微学院公众号 乐分圈微信公众号
乐分圈微信公众号 厕重点微信公众号
厕重点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