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追责对象来看,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从主要追责基层官员向问责包括地方党政主官在内的各方面、各层级官员转型。地方出现的一些生态环境问题表面看来是基层的执法问题,实质上是地方党委和政府的重视程度问题,问责主官要比问责一线执法人员影响力更大。2016年1月在河北试水的中央环境保护督察,问责的对象主要是处级以下的官员,难以克服虚假整改、敷衍整改和拖延整改的现象,环境保护压力传导层层衰减。随着中央对河北省委原书记、甘肃省委原书记、山西省委原书记等省级党委原负责人的处理,被问责的干部级别整体有很大的提高。在部门层面,一些地方的正厅级干部被处理,如湖北省质监局原党组书记、局长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原省农业厅党组书记、厅长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原省经信委党组书记、主任受到党内警告处分;甘肃省林业厅原党组书记、厅长与甘肃省国土资源厅厅长蒲志强等主管受到行政撤职等处分。在地方层面,在第一轮中央环保督察组移交问题追责中,江苏省问责了3个县委书记和3个县长;湖北省也问责了近10名区县委书记和区县长。实践证明,问责地方党政主官和部门主官,对于倒逼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层层传导环保压力,调整产业结构,淘汰落后的工艺和设备,解决“散乱污”问题,促进绿色发展,作用巨大。另外,基层官员对问责的怨言明显减少。
从督察规范化来看,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从专门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督察向全面的生态环境保护法治督察转变。首先,与督察工作相关的法制建设得到加强。中央环境保护督察起步时主要的依据是《环境保护督察方案(试行)》和《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试行)》;2019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规定》,督察工作更加规范化。为了进一步提升督察的绩效,有必要针对现实的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体制、制度、机制和法制问题,采取相应的健全工作。中央结合实际中遇到的问题,修订了《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修改了《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发现和处理生态环境问题违纪违规的党内法规依据更加配套。为了促进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人员廉洁奉公,生态环境部党组还制定了《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纪律规定(试行)》等专门文件。其次,在督察中,为了实施精准问责,防止追责扩大化,相当多的地方党委和政府联合出台了生态环境保护的“党政同责”“一岗双责”的权力清单文件。根据内蒙古、黑龙江、江苏、江西、河南、广西、云南、宁夏等8省区2017年11月16日同步公开的第一批中央环保督察问责情况,地方党委追责46人,地方政府追责299人;在有关部门追责中,环保193人,水利81人,国土75人,林业63人,工信59人,住建51人,城管38人,发改31人,农业9人,公安9人,交通6人,安监4人,国资委3人,旅游2人,市场监管等部门42人。可见,以前由政府主要承担生态环境保护责任的局面以及政府部门中主要由生态环境保护部门承担生态环境保护责任的局面,已经得到一些改变。
从督察体制来看,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正在得到其他机构巡视和督察工作的协同支持,督察的权威性得到进一步增强。2018年6月,中央纪委通报了几起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环境保护违纪违规问题追责情况;2018年全国人大实施了《大气污染防治法》实施的执法检查,该工作被称为环境保护法律巡视;2018年6月,自然资源部作出了几起侵占农地、破坏林地、填海造地、侵占湿地等案件的自然资源督察通报。2018年8月,自然资源部还设立了国家自然资源督察办公室。这些制度化的巡视和督察工作对于配合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的实施,起了重要的协调、促进和保障作用。
目前,我国生态环保从认识到实践正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与此相适应,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正从督促地方端正生态环保态度、打击生态环境违法、营造良好守法氛围为主要任务的阶段,步入强调增强生态环保基础、提升绿色发展能力、促进高质量发展为主要任务的阶段,其制度建设越来越健全,其实施越来越得到深化,其重要领域越来越得到各方面认可。在这一阶段,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作为社会主义生态环境法治制度的重要内容,其有效实施将会有利于2020年污染防治攻坚战目标的实现,并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的目标奠定坚实的基础。
三、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改革建议
2019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规定》。为了进一步提升督察的绩效,有必要针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现实的体制、制度、机制和法制问题,采取相应的改革措施。
(一)健全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法治依据
在督察的法治依据方面,建议修改《环境保护法》,在总则部分规定:“国家实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有关部门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法律责任部分规定:“党员领导干部违反职责规定应追责的,按照《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试行)》的规定执行。”只有这样,才能满足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党内法规与国家立法相衔接的社会主义法治要求,使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法治轨道上长足地发展。
在整改的法治依据方面,建议明确规定督察企业的事由须是法律规定的强制性义务,出台整改的评判标准或者细则,对照验收。对企业和地方重大整改事项的提出,明确规定须经专家论证和督察组集体审议通过而不是督察组工作人员现场表态决定。对于艰巨或者复杂的整改,可以规定分阶段验收。建议主管整改事项的部委加强对地方的整改指导,防止整改走弯路或者整改不到位。
(二)拓展督察的参与主体和督察的对象范围
在督察的参与主体方面,首先,建议全国人大参与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目前全国人大在推行环境保护法律巡视,而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巡视。协调两者关系的方法有二:一是将全国人大的环境保护法律巡视整合进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体系;二是保留全国人大的环境保护法律巡视,但应与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加强衔接,防止增加地方的负担。建议各级人大常委会增加对政府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报告的审议表决程序,并全面公开对政府环保工作的监督信息。其次,建议修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规定》第7条的规定,发挥中纪委(国家监察委)关口前移的监督作用,特别是对督察组是否规范化履职的监督。如果细化其参与程序和案件移送程序,既可规范督察组的具体督察行为,也可发现官商勾结危害环境的案件线索,震慑地方违纪违法行为。
在督察的对象方面,建议在中央开展第二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期间,尽快增补对与生态环保有关部门的督察,发现其对地方和行业开展环境保护指导、协调、服务和监督的不足,然后责令采取制度建设、能力建设等方面的整改措施,使其工作部署和改革措施的推进实事求是,服务于国家绿色发展的大局。对于中央有关部门的督察,建议由曾经担任过省级党委、人大、政府和政协主官的正部级领导干部担任督察组组长,抽调曾经担任过市县党委、人大、政府和政协主官的地方领导干部参与,有利于全面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对于监管和指导不到位的中央部门,由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规定》第24条和第37条的规定提出提升指导、服务和监督地方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质量和高质量发展的整改建议。
(三)理顺自然资源督察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关系
可选择的理顺模式有二:一是设立专门的中央自然资源督察制度,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对各省行政区域开展陆地与海洋自然资源、生态修复与保护、生态空间管控等方面的政治和专业巡视;不再保留国家自然资源总督察办公室,中央自然资源督察办公室设在自然资源部。二是将国家自然资源督察统一于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体系,由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统一开展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方面的综合督察,督察办公室仍然设立在生态环境部。如采取第二种模式,可选如下方式落实具体的自然资源督察工作:一是保留自然资源部下设的国家自然资源督察办公室和几个地区的督察局,在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办公室的统一部署下推进本部门负责的自然资源督察工作。二是自然资源部参与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但不再代表国务院专门行使国家自然资源督察权。
如采取第一种模式,建议修改《环境保护法》和相关自然资源法律法规时,督察的法律依据可规定为“国家实施中央自然资源督察制度,开展陆地与海洋自然资源、生态修复与保护、生态空间管控等方面的督察”,将国家自然资源督察上升为中央自然资源督察。
如采取第二种模式,建议修改《环境保护法》和相关环境资源法律法规时,督察的法律依据可规定为“国家实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开展自然资源、生态保护和环境污染防治方面的督察”。
(四)标本兼督,提升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的能力和水平
在督察事项方面,建议对照《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和其他生态文明建设和体制改革文件的要求,制定标本兼督的督察实施细则。首先,将以下措施纳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规定》第15条第1项规定的督察范围:地方是否开展“多规合一”工作,区域空间开发利用结构是否优化,农业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基础设施是否按期建设和运行,地方的产业结构是否体现错位发展、特色发展和优势发展的要求,规划和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是否衔接,区域产业负面清单制度是否建立。其次,将以下措施纳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规定》第15条第9项规定的督察范围:环保监管机构和人员配备是否健全,环保能力建设是否到位,企业环境管理是否专业化,体制、制度和机制是否改革到位,生态环境监测数据是否一贯真实等。再次,将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是否严格纳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规定》第15条第2项或者第3项规定的督察范围。督察组发现问题后,除了督促地方加强整改外,中央有关部门应加强对地方的工作辅导和财政支持,针对共性问题和个性问题拿出切实的解决、改进或者完善政策。
(五)尽职免责,切实提高督察问责对于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
在问责对象方面,对于生态环境问题与中央部门的工作失误、失职有关的,建议由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提出整改建议,并依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的规定,制定追责机制,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在问责层级方面,被问责的干部层级已有明显提高,最高涉及省级干部;督查问责的县级党政主官和省级政府部门主官比例在提升,得到社会肯定。不过,地市级地方党政主官被追责的还是少见,县级党政主官被严肃问责的比例有待进一步提升。在实践中,市县级党委和政府即使被追责,大多是向上级党委和政府作出深刻检查等较轻的处分。而地方是否真正重视环境保护,市县级党政主官是关键,对其追责不严,必将导致环境保护的压力传导层层衰减,产业结构调整不力,环境保护部署不实。目前在基层,把市县级党政主官作为督察追责重点的呼声很高。
在问责依据方面,要法定与精准。针对生态环境保护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追责,建议由中央统一部署,针对中央各部委和地方各级党委、人大、政府、司法机关及其隶属机构,制定生态环境保护权力(职责)清单,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的要求,建立尽职按单免责制度,减轻生态环境监管人员的思想压力。针对督察组成员的追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规定》第34条第1项有一个情形规定,即“不按照工作要求开展督察,导致应当发现的重要生态环境问题没有发现的”。因为缺乏何为“应当发现的”的判断标准,而且追责也很严厉,即“视情节轻重,依纪依法给予批评教育、组织处理或者党纪处分、政务处分;涉嫌犯罪的,按照有关规定移送监察机关或者司法机关依法处理”,这对于督察组和督察组成员产生很大的思想压力。为了减轻督察组成员的挑错工作压力,提升对地方的精准问责率,建议修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规定》第34条的规定,在“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应当严格遵守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纪律、程序和规范,正确履行职责”之后加上“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及其督察组成员实行尽职免责的制度”的规定。
(作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湖南大学法学院、中国地质大学人文经管学院、首都经贸大学法学院兼职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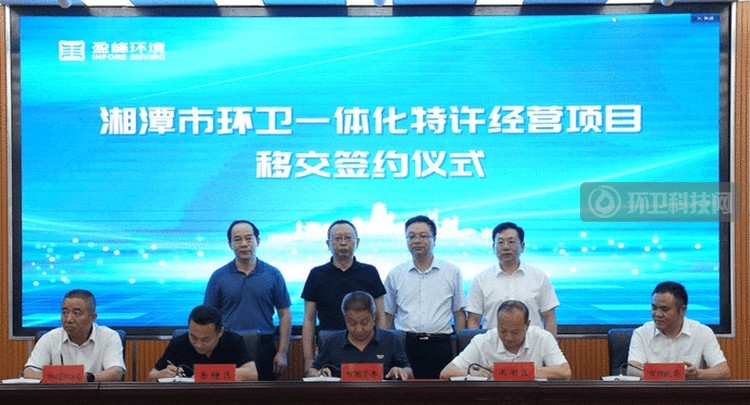



 2020全国厨余(餐厨)
2020全国厨余(餐厨) 2020全国厨余(餐厨)
2020全国厨余(餐厨) 2020全国厨余(餐厨)
2020全国厨余(餐厨) 2020全国厨余(餐厨)
2020全国厨余(餐厨)
 环卫科技网公众号
环卫科技网公众号 环卫微学院公众号
环卫微学院公众号 乐分圈微信公众号
乐分圈微信公众号 厕重点微信公众号
厕重点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