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广岛县来说,为处置福山、府中、大竹等广岛地区的9个市町村的原生垃圾,广岛地区建立了多家RDF工厂。可燃垃圾在经过破碎、分选、干燥、成形等程序之后,变成了直径2.5厘米长约3至7厘米的燃料棒,热值相当于标煤,这样的燃料棒可以成为特别设计的发电厂的燃料。
既然还是要烧,为什么还要把垃圾变成燃料棒?燃料棒工厂的负责人介绍,与普通的垃圾焚烧厂不同,RDF生产实际上是个物理过程,由于温度的控制较低、操作相对简单,所以管理比较容易,可靠性相对要高,对环境的影响小,因而受到了一些地区的欢迎。据当地环保资源部门的负责人介绍,原先这些地区也建立了一些垃圾焚烧厂,目前垃圾处理技术的多元化让他们有了更多选择。不仅如此,垃圾气化焚烧、生化处理等技术的应用在日本已经很普遍,各种垃圾处理技术不断被开发应用。
因地制宜地选择处理方式也让人印象深刻。在鹿岛共同资源化中心,我们看到了RDF的“后半生”。之所以选择在这里设立垃圾综合处理厂,因为附近是个化工产业基地,化工厂、金属冶炼厂产生的废油在经过处理后可以成为发电厂的助燃剂,RDF与可燃建筑垃圾以及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可燃垃圾一起作为燃料用于发电,发出的电又可以回供工厂。
再看看我们处理垃圾的方式,目前基本还停留在日本上世纪40年代阶段,其差距甚远。日产垃圾1.84万吨的北京,对垃圾的处理方式目前还主要依靠填埋,虽然有价值的垃圾要么进入商业物资回收系统,要么被拾荒者捡拾,但是综合处理能力还处在很低的水平。也正是因为填埋场库容的捉襟见肘,才让焚烧等多元处理方式被提上日程。而在这个过程中,焚烧又一直被当成解决垃圾问题的一个重要手段,成为一些决策者们的唯一选项。
北京市《关于全面推进生活垃圾处理工作的意见》中关于调整垃圾处理结构中这样论述:“积极推进生活垃圾焚烧处理,按照垃圾成分、产生量和设施建设规划,2012年垃圾焚烧、生化处理和填埋比例为2:3:5,实现城区原生垃圾零填埋;2015年比例为4:3:3,基本满足不同成分垃圾处理的需要,实现全市原生拉圾零填埋。”垃圾焚烧的比例将在5年之内从2%提高到40%,成为垃圾处理的主要方式。在其他城市,垃圾焚烧也成为重要议题。据统计,在国内已经立项的垃圾焚烧厂超过400家。
要让焚烧成为安全的垃圾处理的主要方式,一些配套的处理设施必须跟上,比如将厨余垃圾分类处理以提高垃圾的整体热值,将有利用价值的废弃物资源化处理,生化处理垃圾的无害化等等。
目前,全国各地的综合处理配套设施正在加紧建设,2010年3月23日,广州首座餐厨垃圾处理厂投入试运行。在北京,继南宫餐厨垃圾处理厂之后,朝阳区的一家餐厨垃圾处理厂也将在年内投运。然而,大城市的综合垃圾处理设施还刚刚起步。可想而知,要从全国层面上实现垃圾的综合处理,还需要较长的时间、巨大的投入和更多的努力。然而思维决定作为,用什么思维指导垃圾处理,选什么方式来解决垃圾问题,这是决定垃圾归宿的根本。我国垃圾累积量已达70多亿吨,80%是靠填埋式,仅占地就达5亿多平方米,尽管这种原始的方式是不可持续且后患无穷,但人们依然乐此不疲。日本有很多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它不仅属于日本,也属于全人类共有的文明。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垃圾处理的先进方式,应给我们带来更多启示。
日本的垃圾运营模式
日本的垃圾运营模式,完完全全是政府主导型,政府切实担当了应尽之责,垃圾处理的员工全部是国家公务人员。由此可见日本政府不仅仅重视垃圾处理,而且也为保护环境舍得投入,使千岛之国永葆靓丽的春色。
如果到日本参观了东京、横滨、广岛等多个地区的垃圾处理设施,就会发现各种与垃圾相关的产业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要么是政府与企业组成利益共同体,要么是政府单独投资——政府的力量一直贯穿于垃圾处理的全过程中。“我们都是公务员,”一位焚烧厂的领导告诉来自中国的参观者。这让人们深感意外。日本的垃圾处理设施大部分员日本的垃圾运营模式工都是公务人员,这不仅有利于监管,而且也明确地告诉公众,这些设施的运营是以政府的信用做担保的,对公众的环保意识也是一个示范。
横滨金泽垃圾焚烧厂的建设方JEE公司的技术人员告诉我们,在日本没有通行的环境标准,各地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标准。垃圾焚烧厂不仅直接控制百姓最关注的二恶英的排放,而且与二恶英生成紧密相关的氮氧化物也被当作最为严格的控制指标。日本把氮氧化物的排放量控制值都在100毫克以下。大阪为了申办奥运,对它的垃圾焚烧厂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氮氧化物的限制设计值为30毫克/标立方,业主方额外要求采用湿法烟气净化系统加触媒脱硝,投资额为此甚至增加了一倍。为了理想的环境质量,政府舍得投入,这是人们对日本各地的普遍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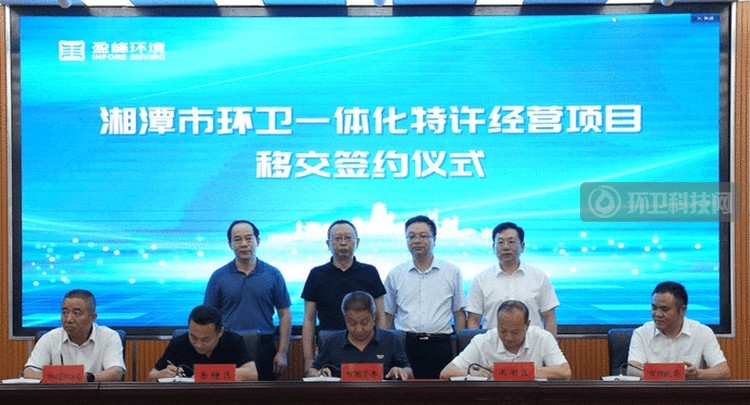



 2020全国厨余(餐厨)
2020全国厨余(餐厨) 2020全国厨余(餐厨)
2020全国厨余(餐厨) 2020全国厨余(餐厨)
2020全国厨余(餐厨) 2020全国厨余(餐厨)
2020全国厨余(餐厨)
 环卫科技网公众号
环卫科技网公众号 环卫微学院公众号
环卫微学院公众号 乐分圈微信公众号
乐分圈微信公众号 厕重点微信公众号
厕重点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