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问题,是人类社会共有的问题,也是城乡居民共同面对的问题,更是政府管理者必须认真解决的问题。垃圾处理关系百姓的生活环境、身心健康,解决不好,可能引发许多社会问题。目前,全国2/3的城市被垃圾包围。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统计,2008年全国城市生活垃圾清运量为1.54亿吨,垃圾处理量为1.34亿吨,不仅数量惊人,而且所谓处理还停留在卫生填埋等低级阶段。而我们的邻国日本,通过推行垃圾分类及综合处理利用,垃圾总量在10多年的时间里下降了近一半,较好地解决了垃圾“围城”、“围村”的问题。日本垃圾处理的观念、制度和办法,对我国正在寻找对策解决垃圾问题应该有所启示。
日本垃圾的分类投送
日本的垃圾分类也是走过一个曲折的过程,他们是在不断探索中总结出一条适合岛国国情的经验做法。目前他们对垃圾的分类做到“投放规定严格,按图轻松分类,处理路径明晰”,效果十分显著,已被日本国民所接受。在日本学习工作八年的本人,回国后对日本垃圾分类投送的记忆犹深:“刚到日本,到当地政府办理临时居住证,同时领到的就是垃圾分类的招贴表格,什么垃圾要放哪儿,怎么放,都得回去仔细看。刚开始还以为这不重要,还像在国内一样把垃圾混装在袋子里,可是没想到,扔出去的垃圾被扔了回来,而且垃圾袋上贴着有关部门的提示,上面写着“你违反了当地垃圾管理的规定,请配合”等字样。这样几次之后,我们才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每人都准备好四五个垃圾桶,扔垃圾也入乡随俗了!”
在日本,对垃圾投放有着严格的时间规定。餐厨垃圾每天最早投放,其余的垃圾也规定了每周固定的投放时间,必须严格遵守。垃圾中转运输站等机构每年年初都会给责任区内的每一个家庭发放垃圾挂历,每天收运什么垃圾,在挂历上都有文字图案标明,一目了然。居民们每天只要按图行事,就可轻松地做到科学分类回收。
资源、可燃、不燃、粗大、有害,日本人把垃圾分成这几大类,每一类的“终点”都有着明晰的路径——可燃垃圾直接送往垃圾焚烧厂,烧完的残渣被运到垃圾填埋场填埋;不燃垃圾经中转站被送往不燃垃圾处理厂,经拆解利用制成再生品,剩余物送往填埋场;粗大垃圾先经专门的破碎处理,可利用成分进行回收,可燃部分送往焚烧厂,剩余部分送往填埋场;资源类则送往再生设施,进行加工利用,生产出再生品;危险类垃圾被送往危险类专门处理的机构。
再来看看我们的垃圾分类:一是系统尚未建成;二是意识还有缺欠。“放两个桶,一个可回收,一个不可回收,然后考验市民的智力,这叫什么分类投放?”在一些城市街头,在居民区内,分类垃圾桶不仅缺少明确的分类指导,甚至连基本的图示都没有,“分类回收”的作用根本没有发挥。对垃圾分类的抱怨似乎不止于此。“管理者对垃圾分类全过程到底怎么做都没有想清楚,就开始忽悠百姓搞分类,最终结果只能挫伤居民积极性。”一位长期倡导垃圾分类的非政府组织从业人员的话虽然有点偏激,却反映了目前北京乃至国内垃圾分类的尴尬。居民垃圾分类后的一系列处理设施、措施的不到位,使得居民垃圾分类工作还停留在随手、随意、随便的“三随”水平。
在北京朝阳区的麦子店社区的居民家中,厨余与其他垃圾分类放置;社区内的垃圾桶分为绿色厨余垃圾、蓝色可回收物和灰色的其他垃圾三种,每个垃圾桶上都用图示标明种类;巡回拉圾收集车将垃圾运送到麦子店北里密闭式清洁站,通过密闭收集运输,厨余垃圾被送到南宫堆肥厂,可回收垃圾通过物资回收系统进入循环,其他垃圾被送到高安屯垃圾焚烧厂。“只要居民分好了,我们保证绝不混装。”北京市朝阳区市政市容委助理调研员张明君说,受居民意识、常识所限,虽然目前厨余垃圾分类量还不多,但这样的试点让预先规划的技术路线完全实现了。由此可见,思路决定出路。垃圾分类并不是一件高新技术活,核心是体制、机制,关键在抓好落实。只有当管理者知道从哪管、怎么管,才能使北京和杭州垃圾分类的试点经验推而广之,更有社会“通用”价值,也只有让老百姓知道为啥要分、怎么分、分什么,才能实现分类链条的无缝对接,才能变为广大民众的自觉行动。
日本垃圾的处理方式
日本垃圾的处理方式已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机制,他们在处理过程就实现减量,使10年垃圾总量减少了一半;处理日趋多元化,主要运用气化焚烧、生化处理、综合利用等;处理方式因地制宜,方式灵活,较好地解决了无害化处理垃圾的问题。
“我们到日本不光是来看垃圾焚烧的。”北京市市政市容委委员张春贵坦率地说,我们看到的是垃圾的综合处理。在东京台场附近的一家垃圾焚烧厂,接待室播放的厂区介绍片,实际上讲的就是日本垃圾的“生命”历程,居民把分好的垃圾投放到指定地点,由垃圾车运往垃圾收集站,经过人工分选、压缩后再送往大型转运站。大型垃圾转运站实际上也是一个资源回收中心,在这里通过机械与人工分选的方式,垃圾量进一步减少。下一步,在大型综合处理厂,分选预处理后的垃圾进入最后的处理阶段,要么直接焚烧发电,或者制成RDF(垃圾燃料库)焚烧发电,最终的残渣被送去填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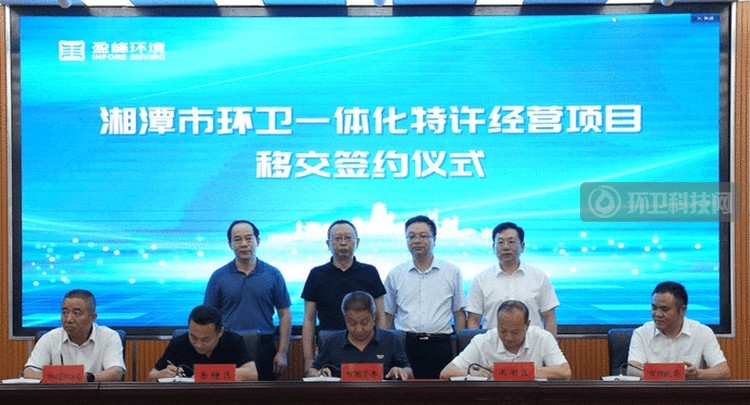



 2020全国厨余(餐厨)
2020全国厨余(餐厨) 2020全国厨余(餐厨)
2020全国厨余(餐厨) 2020全国厨余(餐厨)
2020全国厨余(餐厨) 2020全国厨余(餐厨)
2020全国厨余(餐厨)
 环卫科技网公众号
环卫科技网公众号 环卫微学院公众号
环卫微学院公众号 乐分圈微信公众号
乐分圈微信公众号 厕重点微信公众号
厕重点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