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上文中有所提及,针对垃圾焚烧项目,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标准和监管措施,已通过最大的力度,降低垃圾焚烧项目的污染排放。
退一步讲,即使垃圾焚烧厂会排放一定的有害物质,我们也不能把造成的“健康损失”一股脑推给垃圾焚烧行业。
原因很简单,因为垃圾焚烧是将生活垃圾化零为整了。产生二噁英等有害物质的是“垃圾”,而不是“焚烧”。
需要强调的是,即使不经过焚烧,生活垃圾自身也含有一定量的二噁英。我们需要关注的,是经过焚烧无害化处理后,二噁英是更多了,还是更少了。
去年9月在西安举办的“第八次生活垃圾焚烧处理技术与设备研讨会”上,清华大学刘建国教授作报告指出,生活垃圾自身也含有一定二噁英,需要关注垃圾焚烧是二噁英的“发生器”还是“消减器”。
刘建国教授指出,老旧的垃圾焚烧设施的确是二噁英的发生器,排放的二噁英量是垃圾带入二噁英量的6倍多,其中烟气排放量和飞灰中含量分别为垃圾带入量的1倍和5倍。
而现代化大型垃圾焚烧设施则完全是二噁英的消减器,其烟气排放的二噁英不到垃圾带入量的1%,飞灰中的二噁英含量也小于垃圾带入量的10%,总体消减了80%垃圾中原有的二噁英。
数据显示,欧盟生活垃圾焚烧对二噁英排放总量的贡献由1990年的11.5%降低为2015年的0.004%,削减了99.99%。
美国生活垃圾焚烧量由1987年的1340万吨上升到了2000年的3060万吨。但其对二噁英产生总量的贡献却由1987年的63.8%降低为2000年的5.9%,削减了99.1%。
日本的生活垃圾焚烧二噁英排放量由1997年的约5000gTEQ下降到2003年的71gTEQ,削减了98%。
这些趋势说明,随着技术进步标准提升,生活垃圾焚烧二噁英的排放是完全可以得到有效的控制。
刘建国教授报告中还援引了一项研究数据,南京大学针对我国222个垃圾焚烧厂核算其二噁英平均排放因子为1.2ug/t垃圾,比垃圾自身二噁英含量低1个数量级,证明垃圾焚烧实际上大大削减了向环境的二噁英排放;二噁英致癌风险只占总致癌风险<10-7,说明其环境风险可接受。另外,垃圾焚烧过程中主要致癌风险来自铬元素(Cr),而焚烧过程中并不会产生丝毫的Cr,所以如果不经过焚烧风险其实更大。
综上所述,如果想计算垃圾焚烧中的“隐秘成本”,正确的方法应该是计算原生垃圾如果不经处理造成的危害,与焚烧后的风险进行对比,这才能得到更加公允的论断。
垃圾焚烧是一个带有社会公益属性的产业。就像一个生病的病人去医院做手术治疗。
这一过程中,我们只计算病人的诊疗费用和手术带来的痛苦,而决口不提对患者带来的健康收益,那我们得到唯一的结论,就是医院黑心、医生无德,这当然是严重的偏颇。
垃圾焚烧技术是目前世界各国主流的处理生活垃圾的方式,不仅高效,还能产生一定的电能作为回收利用。
不可否认,这一技术在发展过程中,曾因为认知水平的不足,造成过一些环境损害。但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的垃圾焚烧技术已经步入世界前列。国家和企业正通过一系列举措,提升技术、加强监管,将风险控制在“可接受”范围,需要我们客观的去评价。
就像人人都知道修建高速公路的好处,但每一条高速公路上,都会有发生车祸的风险。
我们要做的,是对高速公路的设计、建造严格把关,平时注重科学管控,把风险降到最低。而不是放大风险本身,停止高速路的建设或者不敢开车上路。
绿色和平文章中,充斥着对我国的生活垃圾处理产业的诟病,但因缺乏充足的论据和专业性,令人遗憾。而对于垃圾焚烧行业的点评,只以管窥豹式的解读,片面夸大危害性。
笔者认为,这样的观点不仅是对生活垃圾处理行业的伤害,由此令公众对产业产生错误的认知,则贻害更大。












 2020全国厨余(餐厨)
2020全国厨余(餐厨)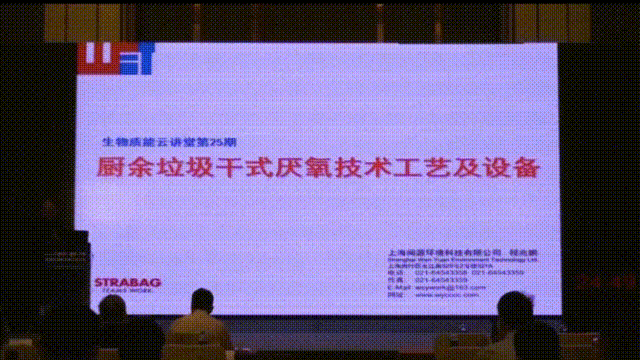 2020全国厨余(餐厨)
2020全国厨余(餐厨)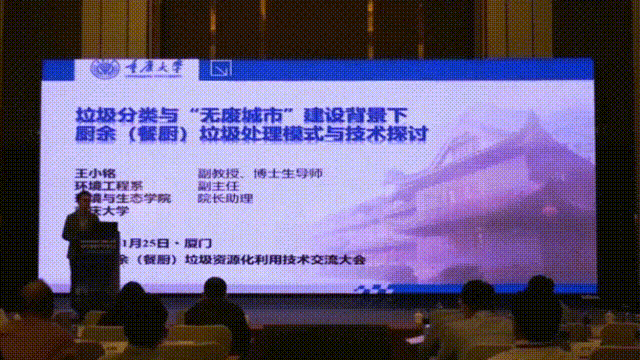 2020全国厨余(餐厨)
2020全国厨余(餐厨) 2020全国厨余(餐厨)
2020全国厨余(餐厨)
 环卫科技网公众号
环卫科技网公众号 环卫微学院公众号
环卫微学院公众号 乐分圈微信公众号
乐分圈微信公众号 厕重点微信公众号
厕重点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