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邻避”设施通常都建在“人少偏远”的地方。说起来,无论从技术与风险上,还是道义上,建在“人少偏远”的地方都是“最佳”的选择。但是,“人少偏远”的地方为何是“最佳”的选择?偏远而人少哪怕只有一人生活的地方,就一定可以承担“邻避”设施所带来的风险或环境的代价吗?实际上,这是以“公共性”名义压迫弱者的行为。更何况事实也并非完全如此。2014年4月25日,杭州本地媒体称中泰此地300米内只有25户居民,5公里外才有楼盘小区。事实与此相去甚远:“与规划的焚烧厂紧挨的就有4个村,包括南峰村、南湖村、中桥村和白云村,总人口约上万人,其中,中桥村距离选址大概只有2公里。绝不是像媒体报道所说的‘人烟稀少’。” 5公里外的中泰街道中心则更是人口聚集、楼盘小区林立。规划建设垃圾焚烧厂的消息影响了不少人的购房。
相对于政府尤其是中国政府来说,任何公民、任何群体、任何组织都是弱者,都处于弱势。因此,“邻避”运动是弱者的一种武器。在“私民社会”中,个人的利益、私权最容易被忽视、被侵犯,并且也最难得到纠正。在中泰垃圾处理厂事件中,杭州市政府一直强调技术的安全性。但是,民众反唇相讥,既然技术上有如此保障,那么为何不建在市政府的边上,或者建在政府公务人员住宅区边上?如果政府这次这样做了,那么就会给全社会树立一个好榜样,可以保证从今以后,类似的“邻避”设施的建设不会出现大规模对抗性的“邻避”运动了。更何况,一旦垃圾处理厂建成后,大量将来自于城区的垃圾运往垃圾处理厂的运输费可以节省下来。
因此,作为弱者,不得已只好将抗争作为斗争的武器。“私民社会”是一个缺乏组织性的社会,这个社会加上政府公信力似乎已经陷入“塔西陀陷阱”之中了,容易走向群体性的暴力对抗。
解决之道:从“私民”走向“公民”
道德主义、理想主义无助于中国“邻避”运动的解决。与“邻避”运动没有关联的民众包括媒体,往往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批评参加“邻避”运动的人不以国家大局或公共利益为重,指责其自私。指责者唱起道德高调,实际上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突出了他们的“虚伪性”和“伪公共性”。“在现实生活中,‘公’的重要,并不在于无视或否认私欲、私利,从而设法抹煞私人利益、取缔私人领域,而在于‘公’能够代表众人之私,实现众人之私,亦即‘公’的出发点就在于保障个体权利、维护个体利益。‘公’的观念以公民身份为前提,本身就蕴含着此种意味。”以“私民社会”分析“邻避”运动,并非就是简单地否认“私民”本身的意义,也不是否认中国“邻避”运动的价值。讲“私民”本身对于中国来说是一种进步,是对计划经济时代那种虚假的“大公无私”的一种拨乱反正,是对正常人性的一次复归。也许,“私民性”的“邻避”运动是中国走出虚妄的“大公无私”,而走向“公民社会”的一个必经过程。而怀着理想主义的人,相信只要做到决策过程透明,让多元主体共同参与讨论和评估,取得最大公约数,充分照顾各方的利益需求,“邻避困境”这一世界性难题就有望得到破解。但是,问题在于,这个结果如何得到?解决之道在何处?
现实主义的路是理解、妥协、共识与合作。那么,如何达成共识走向合作?这就要回到基本的路径,那就是咨询与决策的透明性、公共参与。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政府,球在政府的脚下,也控制在政府的脚下。而透明性、公共参与需要制度与法治的保证。例如,有关信息公开性与透明性,需要有法律上的明确规定。这方面纽约等地的经验可借鉴。1991年,美国纽约市施行《城市设施选址标准》,执行“平等共享选址程序”,让多元主体共同参与讨论和评估,取得最大公约数,充分照顾各方的利益需求,成为公众合适参与的成功典范。来源“探索与争鸣杂志”微信公众号(ID:tansuoyuzhengm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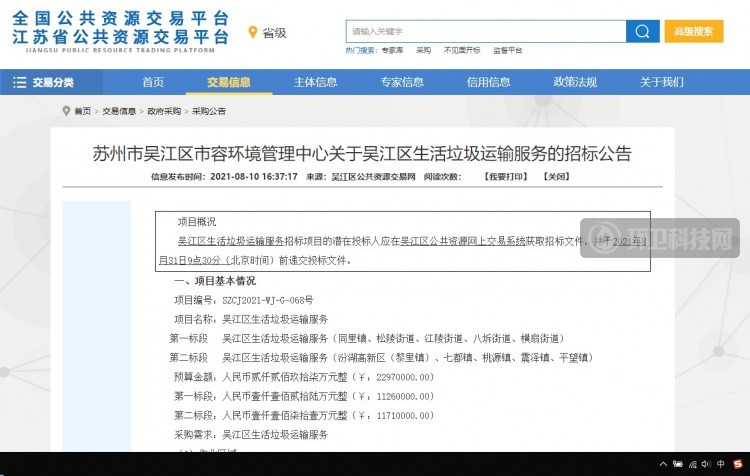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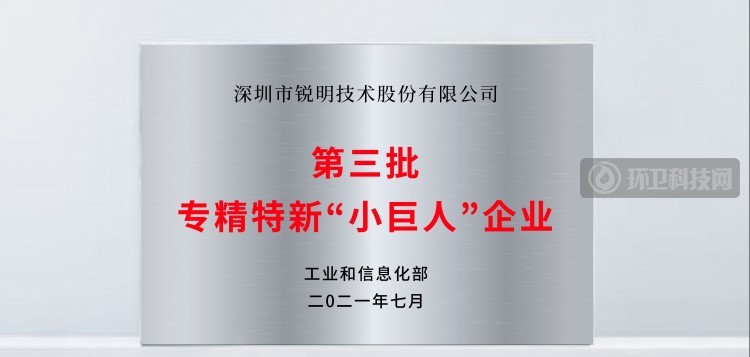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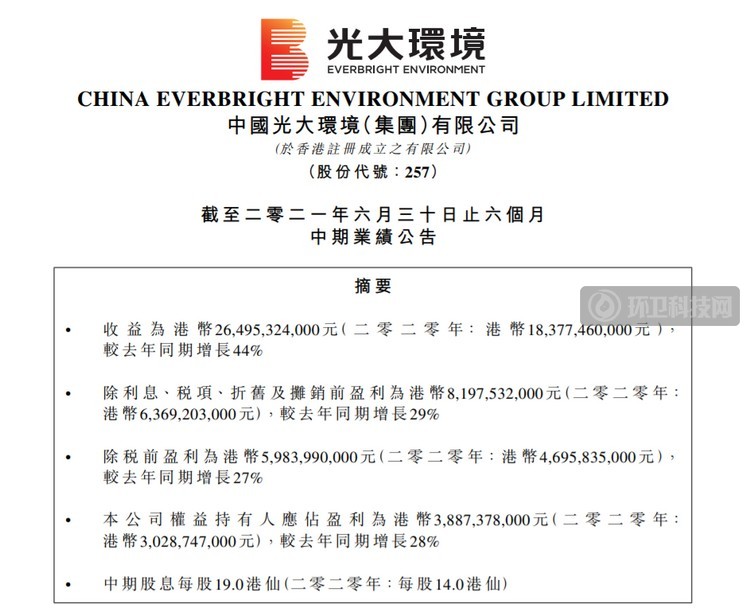

 盈峰环境排水抢险车赴
盈峰环境排水抢险车赴 2020全国厨余(餐厨)
2020全国厨余(餐厨) 2020全国厨余(餐厨)
2020全国厨余(餐厨) 2020全国厨余(餐厨)
2020全国厨余(餐厨)
 环卫科技网公众号
环卫科技网公众号 环卫微学院公众号
环卫微学院公众号 乐分圈微信公众号
乐分圈微信公众号 厕重点微信公众号
厕重点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