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这种“私民”所从事的“邻避”运动只能属于自由主义意义上的,而非“社群”主义的范畴。自由主义假定的是一个以自己个人私利为中心的公民个体形象,而共和主义假定的则是一个以集体利益为优先的共同体成员形象。公民共和强调,政治的真正体现是公民们在公共领域内协商共议群体公共事务。政治行为的价值不在于达成实用性的协定,而在于它能实现每个参与者的公民主体性,锻炼他的判断辨识能力,并在与他人的关系和共同行为中成为群体有效成员。显然,阿克曼的企图是将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调和起来。如果我们仍然用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的二元论来进行分析的话,那么,中国民众在“邻避”运动中呈现出来的就是自由主义的个体形象。
当代社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人与人的交往在扩大,共同利益在增加,我们必须共同地生活。但是,我们并没有转向到“公共生活”之中。我们“共同生活”是我们为了维护各自的利益和满足自己的需求——而不是基于“共同善”——“不得不”共同生活。“共同生活是‘形聚神散’,只是个人意志和欲望的集合体。但公共生活则不同,它是以公共利益、公共目标、公共善的存在为基点的。”时至今日,虽然人们的公民意识正在逐渐增强,但普遍存在的公共意识淡薄、公正态度缺失和公益精神不足,却依然是不争的事实。
中国式“邻避”运动还展现出另一面,就是中国公众参与的“非组织性”。在现代社会中,积极参与公共事务是公民的权利,也是每个公民的义务,而公民的公共参与可以切实保障公民的权利。但是,“私民社会”下的公共参与是非组织性的,有组织性或高度组织性的都是国家或政府的行为。冯仕政通过实证的数据表明,超过七成的民众从来既不参与官方组织的活动,也不参与民间组织的活动:“当前中国公共参与的一个重要特征恰恰在于,公民组织很不发达,公共参与一般不是以组织为基础,而是个体化的、非组织化的。”他指出:“私民观念及其支配下的政治行为使公民不能形成整体力量对国家的权力形成有效约束。”这样一种非组织化的公共参与状况,非常不利于社会矛盾的化解,尤其是不利于社会冲突的组织化、程序化解决。社会利益的非组织化不但不会消除,反而会提高发生大规模集体行为的可能性。最近几年来,中国发生了多起震惊全国的骚乱事件,比如安徽池州事件、重庆万州事件、四川汉源事件。这就是“大散众”形成大规模集体行为的现实例证。
3“私民社会”中弱者的武器
在全能主义政治下的中国,“私”的财产权缺乏正当性。作为社会弱势群体的农民,“即便意识到自己的利益受到侵害,也几乎无人敢在有形无形的政治高压下公开表达不满”。实际上,现在“邻避”设施地址的选择依然是强势者的逻辑,即便在西方,“垃圾处理场往往被放置在相对弱势的社区”,“具有嫌恶性的邻避型设施最终地点经常是落于较落后或是政治势力较薄弱的地区”。中国大多数邻避设施在建设中“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误区是,政府照顾大多数人利益,想当然地认为小部分群体应该牺牲和付出。中国向来重视集体利益,对小部分个体的意见不以为然”,“一些城市近年来通过邻避抗争取得成功的案例较多,而农村受害者抵抗环境污染侵害却显得无力。中国城乡邻避抗争存在差异,致使垃圾处理项目正由城市向农村或郊区迁移”。
西方学者已经点明“邻避”的标签性及其背后的“压迫性”。Maarten Wolsink认为,“Not in My Back yard”这个带有强烈贬义色彩的描述,也成了当权者削弱抗议运动合法性的重要话语工具。以杭州市规划局官员的话来说,这是不得不作出的选择,那里的居民要识大局:“目前,西部片区只有一家垃圾焚烧厂,由于建设时间比较早、城西人口数量与日俱增,现在已处于超负荷状态,处理能力跟不上城西区块的垃圾产生量,且无地扩建。因此,急需新建一个垃圾焚烧厂。”杭州中泰乡的九峰是相对合适的一个位置,除该地块外,已别无他选。漳州古雷PX爆炸事件就是弱者的悲剧。2015年4月6日福建漳州古雷港经济开发区腾龙芳烃项目发生漏油起火事故,引发周边罐区三个储油罐爆裂燃烧。这个项目原计划于2007年建在厦门。由于当地居民的强力反对而不得不迁到现在发生事故的漳州古雷。厦门人庆幸自己当年的勇敢与执着。漳州古雷PX项目爆炸,某种意义上说,又是一桩弱者的悲剧。因为相对于厦门人来说,漳州人是弱者。














 盈峰环境排水抢险车赴
盈峰环境排水抢险车赴 2020全国厨余(餐厨)
2020全国厨余(餐厨)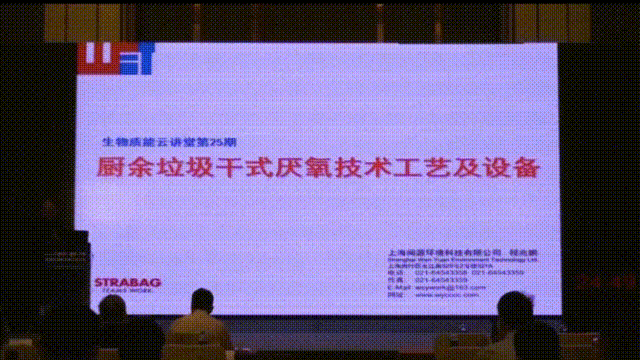 2020全国厨余(餐厨)
2020全国厨余(餐厨)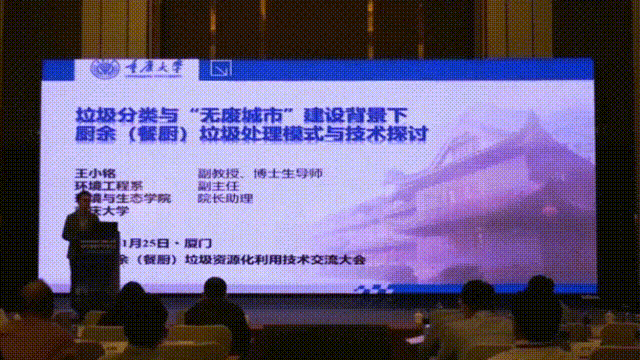 2020全国厨余(餐厨)
2020全国厨余(餐厨)
 环卫科技网公众号
环卫科技网公众号 环卫微学院公众号
环卫微学院公众号 乐分圈微信公众号
乐分圈微信公众号 厕重点微信公众号
厕重点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