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私民”或“私人”,当然首先相对于“公民”概念而言,它是指以个人取向为主导的民众,其言论和行为以关注和满足个人或小群体的利益、情感、意志为主要目的。所谓“小众”与之基本同义。公民当然是一个自然人,但是一个自然人如果不涉及国家公共事务而只局限于私人事务,其身份就不是“公”民而仅是“私”民。进入“邻避”运动中的私民之“私”,并非仅仅一己之私利,体现出一些有广泛性的愿望,其中包括非“邻避”设施直接相关者的愿望,但实质上是追求私人生活的目标,“没有关于普遍的人际关系尤其是政治关系的正面诉求,私人之间也没有先在的共同目的”。此外,私民之“私”并“不试图就公共政治问题进行公共推理,不打算为自己的行动提出可以为大家所共享的理由”。
这种“私民”就是美国宪法学者阿克曼在《我们人民:宪法的根基》中所提出的“私人公民”(private-citizen)概念。在他看来,大多数美国人兼有私人公民和公共公民两种角色,但在不同的时间点上扮演不同的角色。大多数时间,这些民众是私民,私人公民属于常态政治时期的美国公民定位,这一类人作为普通公民主要关注自身生活,关注私人事务,在参与政治事务方面较为被动,难免自私、冷漠和狭隘。但是,他们在关键的时刻也并不排除能够主动地参与政治事务,成为公共公民。
周而复始,一次次“邻避”运动的出现,一次次教训,就是没有进步:过程相似,结果相同(要么政府妥协,要么政府秋后算账)。问题在于为什么没有进步,无论对于政府还是公众,为什么没有能够吸取教训?原因在于我们还没有形成一个公民社会,我们是“私民”,社会还是一个“私民社会”,没有公民社会的良好根基。公允地说,倒是政府在吸取教训,有了进步,例如决策的透明性增加,越来越慎用暴力来对抗暴力,搭建让公众参与的平台。但是事件还是一件一件地发生。问题自然有政府的一面,但是,深层次的却是社会处于“私民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我们都是“私民”。尽管今天的中国在经济、政治、思想等许多方面都开始“世界化”了,但是从国民性角度观之,我们依然停留在“私民”的水准上,没有成为现代社会的合格“公民”。人们不难看到或想象到,即便政府给了公众平台,但公众往往难以达成共识。
讲中国“邻避”运动的“私性”并非作道德上的批评。即使在西方以代议制为核心的民主社会,也免不了“私性”侵蚀“公民性”(citizen)或“公共性”,西方社会也不时出现公民的私利主义(civic privatism)。事实上,约翰•密尔早就看到了这一点。他预测秘密投票会鼓励公民把选票当成商品贩卖,以达成私人的满足,也就是说秘密投票只会使投票者选择对他私人有利的候选人,而不会选择对国家和公共有利的候选人,因此,密尔的想法是:公开讨论会鼓励大家关注公共利益。西方不少学者承认,西方的社会每次选举几乎只看到“私”民而没有“公”民,一再印证了密尔的想法。
2“邻避”运动背后的非“公意”和非“组织性”
“邻避”运动显现出特殊主义的个体自由价值观,没有超越性,只是“众意”,而非“公意”。按照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说法,社会中的人具有双重身份:一方面是作为主权参与者的公民而存在,另一方面是作为自然人而存在,这样就相应地产生了两种意志:公意(general will)和众意(particular will)。作为公民而产生的意志为公意,它以共同利益为基础、着眼于共同的善;基于自身而产生的意志为私意,它力求促进和实现个人利益。
在私民社会中,公众是一个个特殊主义的个体。这就可以解释在传统中国,在家庭或小共同体中的人们是“无私”,面对统治者他们是“臣民”,而在共同体之外却是没有“公”的,这就是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同心圈”理论。这也就是近代以来梁启超这些思想家们所批判的对象。在1949年后,人的“私性”与“私民社会”被有效地压制住了,直到改革开放后得以再次展现。但是,改革开放前的年代既没有“私民社会”,也没有“公民社会”,因为社会本身已经完全消融于党国体制之中而不见了。在私民社会中,只有“众意”而没有“公意”,只是利益相关者的“意见”之合,“邻避”运动本身并非是为了环保,为了生态的正义性,为了整个社会福祉。这中间也许会有“公意”之闪耀,但毕竟不是“公意”之本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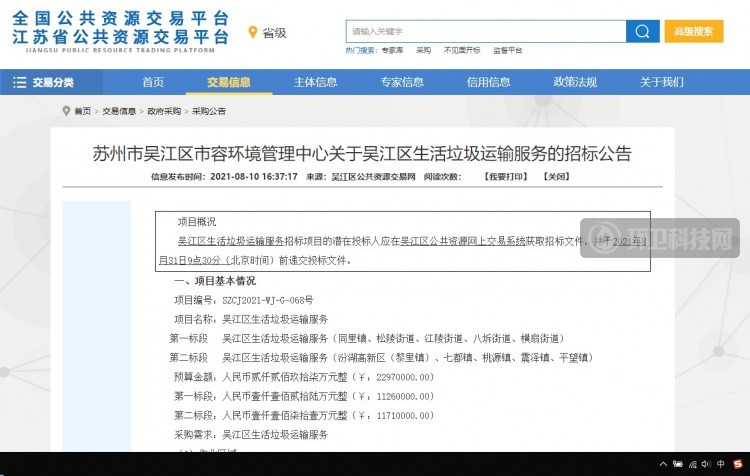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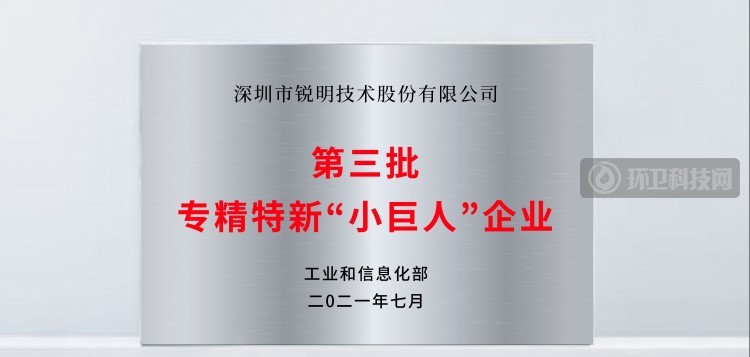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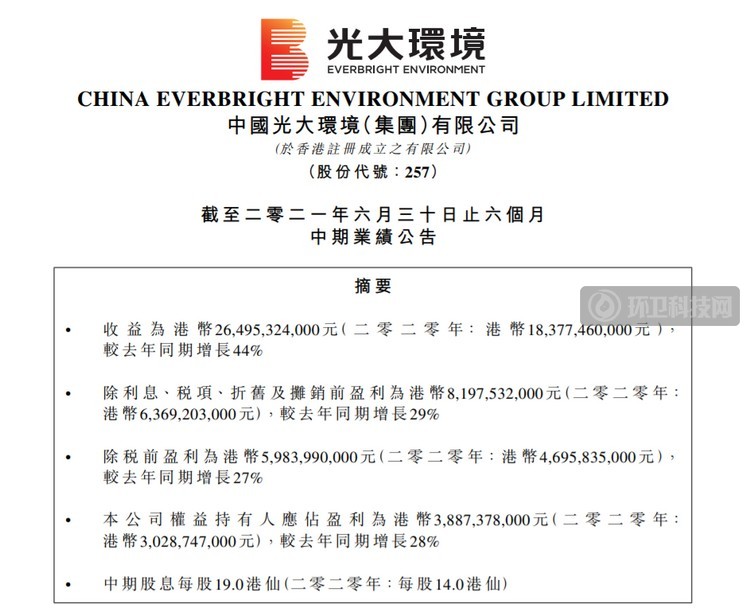

 盈峰环境排水抢险车赴
盈峰环境排水抢险车赴 2020全国厨余(餐厨)
2020全国厨余(餐厨) 2020全国厨余(餐厨)
2020全国厨余(餐厨) 2020全国厨余(餐厨)
2020全国厨余(餐厨)
 环卫科技网公众号
环卫科技网公众号 环卫微学院公众号
环卫微学院公众号 乐分圈微信公众号
乐分圈微信公众号 厕重点微信公众号
厕重点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