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以“私民”与“私民社会”可以解释“邻避”运动在中国的出现、频发及运动的实质,可以对以上这些解释作补充。
中国式“邻避”运动中的“私民”与“私民社会”
“邻避”运动最早出现在城市化过程中的欧美国家。起因是垃圾处理厂等市政、工业设施在建设中,时常遭到附近居民的强烈反抗。居民的诉求通常是“别建在我家后院”。在亚洲,“邻避”运动首先现身于日本。随后,中国台湾、香港等经济发达地区也迎来了这一浪潮。
近十年来,中国大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环境治理问题日益突出,发生了多起引起官方和学术界关注的“邻避”运动。学者们对这些事件的发生过程作了梳理与分析,例如,较为“固定”的模式是:民众街头抗议—政府压制—抗议升级—政府妥协—抗议结束。然而最终项目仍然开工,工厂仍然开建,这显然不是终结“邻避运动”的理想路径。梳理出事件的过程常常是事后诸葛亮,因为发生于中国大陆的这些群体性事件通常都不是事先规划好的,其实是没有第一阶段、第二阶段或者什么第三阶段,等等。不过,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看,这些运动还是存在着一些所谓“标准化”的程式,即三阶段式:第一阶段,政府为尽量减少阻力,一般都是在公民事先不知情的情况下公布某个大型项目开工的消息,随后项目周边的居民开始通过各种合法的渠道进行抗议;第二阶段,在体制内的申诉途径无果之后,居民一般会组织起来进行大规模的集会游行,采取横幅抗议、聚集政府大楼门前等方式进行抗争,而政府也会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压制,导致事件升级,整个事件被推向高潮;第三阶段,在项目周边居民和全社会的舆论支持下,政府迫于压力和居民进行协商对话,经过充分的利益博弈后,政府出于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一般会作出让步,宣告“邻避”设施停建和迁址。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运动的结束,在此之后,有些宣布停建的项目又重新启动,一些迁址后的项目或者新建的项目也会同样遭到当地居民的反对,随即又开始新一轮的“邻避”运动,如此循环往复。
从2005年4月浙江东阳市画水镇居民反对工业区环境污染所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到2014年5月浙江杭州余杭民众反对建立垃圾焚烧厂并发生群体性事件,时间过了十年。尽管时间过了十年,但似乎没有大的变化或进步。为什么呢?
1“邻避”运动背后的“私民性”
首先,让我们对于杭州中泰乡垃圾焚烧厂事件作一个定位,中泰抗争属于共识中的分歧:公众认识到建造垃圾处理厂的必要性与紧迫性,这是共识,分歧在于建在何处。杭州市政府所提供的资料与数据表明,近年来,杭州市区垃圾年增长率在10%上下,2013年杭州市区生活垃圾处理量达308万吨,日均8456吨。天子岭垃圾填埋场设计规模2671吨/日,到2014年5月事发之时,最高日填埋量已达5408吨,超出设计能力1倍以上;若仍无新增垃圾末端处置能力,预计只能再用5年。新建垃圾焚烧厂已经迫在眉睫,刻不容缓。因此,分歧不在于要不要建而是建在什么地方。有关“邻避”设施建设的分歧是共识下的分歧,因此,分歧实际上是公众与公众之间的分歧,而不是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分歧。对于政府来说,是选址的问题,不是建在A就是B,但是对于公众来说,就是“邻避”,不要建在我家后院,其他地方都可以,就是非A,其他B、C、D都可以。
那么,为什么有相当共识的事却会产生严重冲突的群体性事件?难道只有对抗与冲突一条路可走?共识中有分歧,说明共识本身的脆弱性,因为这种所谓的共识只是基于直观的生活感觉、经验,而不是通过理性的沟通和深思熟虑达成的,是一种情感性的认知。当感受与自己的利益不一致或相左时利益会压倒共识。即便退一步说,在利益面前,个人利益的选择会优于共识的坚守,出现“邻避”现象自然可以理解。但是,这种“邻避”行为并非就一定要通过群体性对抗形式表达出来,通过暴力对抗引起社会的关注,从而达成问题的解决,至少朝着自己期待的方向发展。共识本身的脆弱性,实质是“私民性”,可以用阿克曼教授的“私人公民”来解释。
中国的“邻避”运动参与者不是“公民”(此处的“公民”不是法律意义的“公民”,而是政治学意义的),而是“私民”,是“大散众”。事实上,西方学者也曾经指出过,“邻避情结”是一种自利的、意识形态的或政治的一种倾向。冯仕政指出:“中国人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传统臣民观念的影响,开始树立起现代公民观念。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中国人仍未摆脱私民观念的影响。”中国的“邻避”运动是一种非“公民运动”,是“私性”的一次展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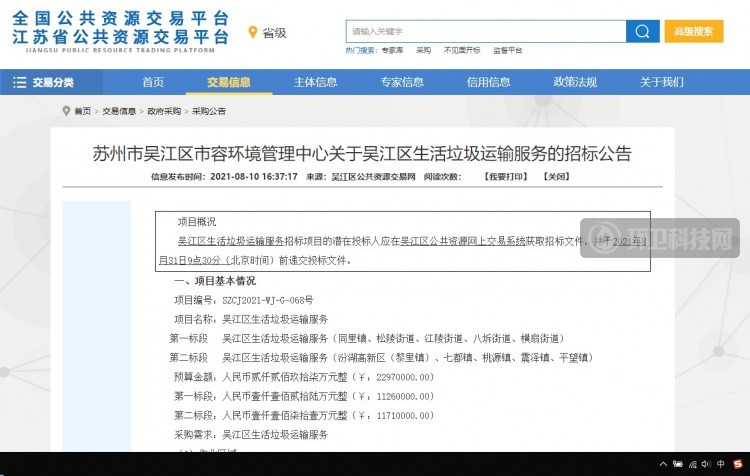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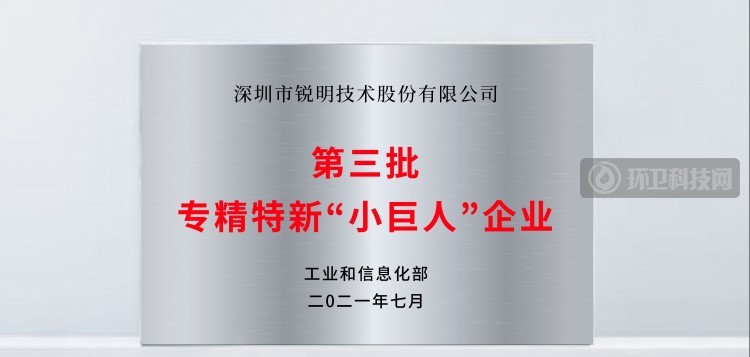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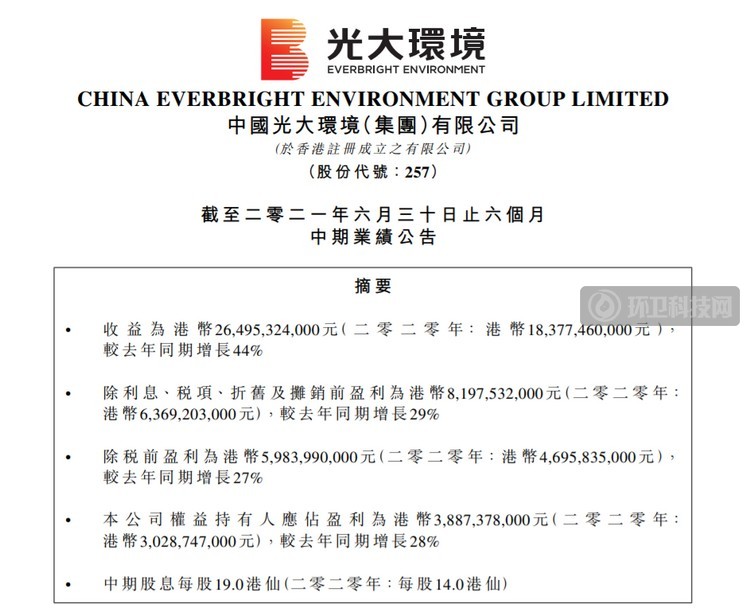

 盈峰环境排水抢险车赴
盈峰环境排水抢险车赴 2020全国厨余(餐厨)
2020全国厨余(餐厨) 2020全国厨余(餐厨)
2020全国厨余(餐厨) 2020全国厨余(餐厨)
2020全国厨余(餐厨)
 环卫科技网公众号
环卫科技网公众号 环卫微学院公众号
环卫微学院公众号 乐分圈微信公众号
乐分圈微信公众号 厕重点微信公众号
厕重点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