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这些分析有相当的合理性和解释力。但是,这些不是“邻避”现象涌现原因之全部,甚至不一定是其根本。本文重点也放在如何解释中国式“邻避”现象,因此对以往文献的批评也集中于解释性的因素。
(1)从纵横比较的角度来看。从纵向角度来看,“邻避”现象涌现之前,中国也有不少应该产生“邻避”运动的建设项目,毛泽东时代有,改革开放前期也有不少,可是并没有出现引起社会关注的“邻避”运动,更没有出现“邻避”运动涌现的现象。事实上,计划经济时期,环境问题已经初现,但是集体沉默。人们可以解释,在那个年代,人们受大公无私的意识形态教育。人们也可以解释,在那个年代,公众没有机会发生“邻避”运动,因为不敢,否则就变成反党、反社会主义了。曲格平说过,“当时我国在政治上并不承认存在污染,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不可能产生污染,谁要是说有污染,谁就是给社会主义抹黑”。在政治教化下,人们对工厂污染虽有抱怨和不满,却无人敢于公开表达,“因为这是国家的工厂,提工厂的意见就是提国家的意见,自己不就成了人民的敌人了吗?没人敢提!”有一些学者用“政治机会结构”来解释,过去没有而现在有了政治机会。问题在于政治机会只是一种可能性,即使有将这种机会变成现实的条件,为何非得对抗性的形式不可,并且结果通常就是以暴力结束暴力的抗议或者以暴力威胁而结束?世风变了,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对于有些破坏生态、污染环境严重的项目,不仅政府大力引进,而且当地百姓也欢迎,不见得有什么反对的“邻避”运动。从横向比较来看,“邻避”运动是世界普遍存在的,不只是中国特有的,问题是,普遍存在的“邻避”运动在中国的独特性在于:一是近几年特别的多,可以说是集中爆发,为世界各个区域所少见;二是对抗性,中国的“邻避”运动常常变成暴力对抗的群体性事件。为何这几年在中国集中爆发“邻避”运动,并且往往以暴力对抗的群体性事件形式出现?
(2)政府决策与信息不透明。这是一个很好的解释因素。例如,Wanxin Li、Liu Jieyan和Li Duoduo三位通过三个案例表明,在中国社会缺乏允许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制度框架,而中国政府也只是被动地反映公众的要求,没有作出制度的承诺让公众参与,他们的结论是没有公众参与的公共决策注定会蒙上缺乏正当性的阴影。问题在于,政府已经在不断改进,包括完善相关的参与机制,但是“邻避”运动依然此起彼伏。例如,2014年杭州市政府就余杭区中泰垃圾焚烧厂建设提供了36个问题的咨询,其中包括杭州为什么要新建垃圾焚烧厂,垃圾焚烧废气污染如何防治,二英检测执行什么标准,垃圾渗滤液怎么处理,垃圾焚烧厂臭味如何控制,等等,极为详细。因此,板子不能只打在政府身上,这样并不公允。事实上,王奎明和钟杨的实证研究也表明了这一点:基于全国规模的民意调查研究发现,不同于西方国家,我国“邻避”运动为“议题单一型”,即从民众参与“邻避”抗争活动的意愿角度而言,“邻避”设施本身是民众关注的唯一议题,而政府议题包括政府环保信息公开度、政府公信力、政府治理环境表现均为非显著性相关因素。
(3)环境保护意识增强。这是当然的。全民环保意识普遍增强,而不只是与“邻避”设施相关联的区域民众的环保意识提高了。事实上,也没有任何实证数据证明,发生“邻避”运动的地方民众在环保意识上比其他地方的民众更强。所以,问题恐怕主要不在于环保意识上。
(4)认知上的问题。国外有不少的经验研究表明,对于风险不确定性的认知问题导致“邻避”运动的出现,这确是一个问题。但是,在网络技术如此发达的今天,相关咨讯信息可以很便捷地获得,更何况专业人士和政府相关部门都会提供。问题恐怕主要也不在于认识和信息,而是一种对于科技主义的反抗。
(5)利益因素。这自然是最有力的解释因素了。改革开放初期,人们对于造成自家环境污染的项目不反对甚至表示欢迎,为什么?是出于利益之考虑。但是,现在为什么会出现“邻避”运动?当然,也是出于利益之考虑。同样是利益,为什么结果不同?原因在于一个是有明确边界的共同体利益,有着直接关联的利益;另一个是公共利益,非直接的利益。我们不难看到,但凡与利益有着直接关联的且有明确边界的,即便会产生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人们也不会反对,更不会出现“邻避”运动,可是与公共利益有关并且即使有技术政策保障的、但不增进本人利益的项目就会产生“邻避”运动。这说明什么?说明中国依然还是一个“私民社会”,还不是一个公民社会。“私民社会”下产生出了中国的“邻避”运动。在中国,“邻避”运动只是人数众多,但不姓“公”,不是“公民”运动,而是姓“私”,是“私民”的聚集。对于“邻避”现象的产生,恐怕近乎是人本能的反应,没有人愿意在自家后院建造“邻避”设施,这与道德没有一丝的关联。利益可以解释,但不能解释全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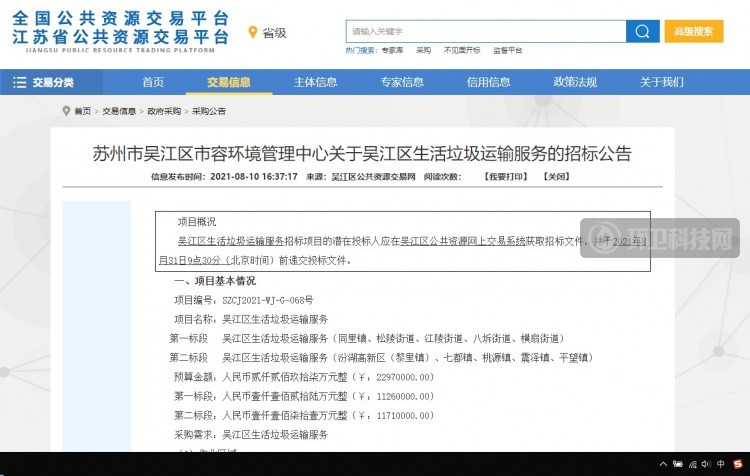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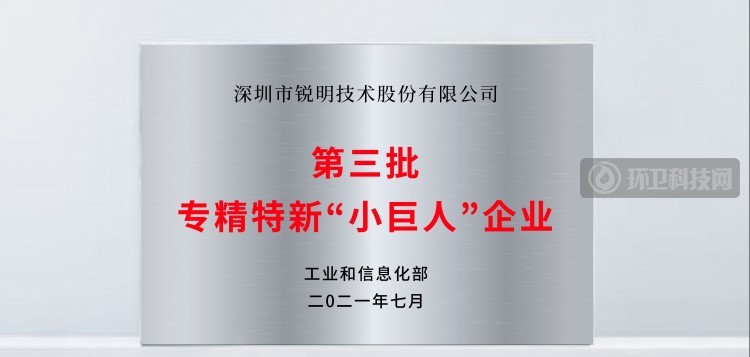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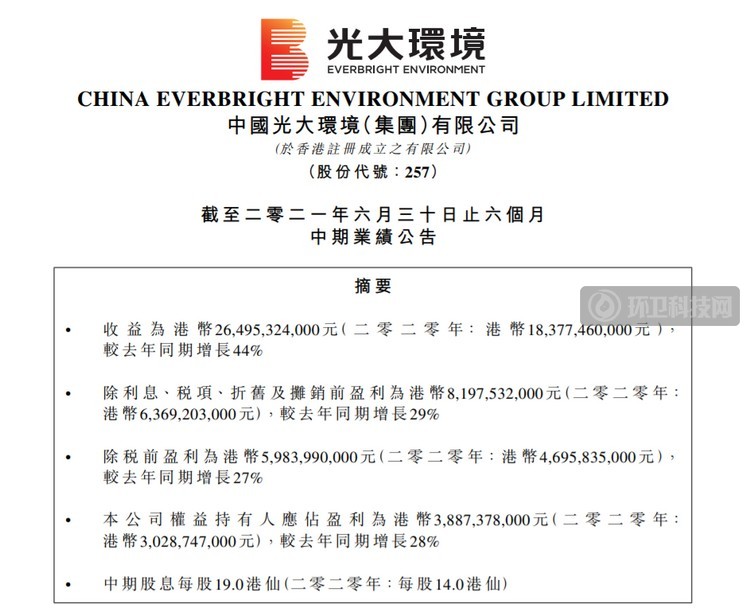

 盈峰环境排水抢险车赴
盈峰环境排水抢险车赴 2020全国厨余(餐厨)
2020全国厨余(餐厨) 2020全国厨余(餐厨)
2020全国厨余(餐厨) 2020全国厨余(餐厨)
2020全国厨余(餐厨)
 环卫科技网公众号
环卫科技网公众号 环卫微学院公众号
环卫微学院公众号 乐分圈微信公众号
乐分圈微信公众号 厕重点微信公众号
厕重点微信公众号

